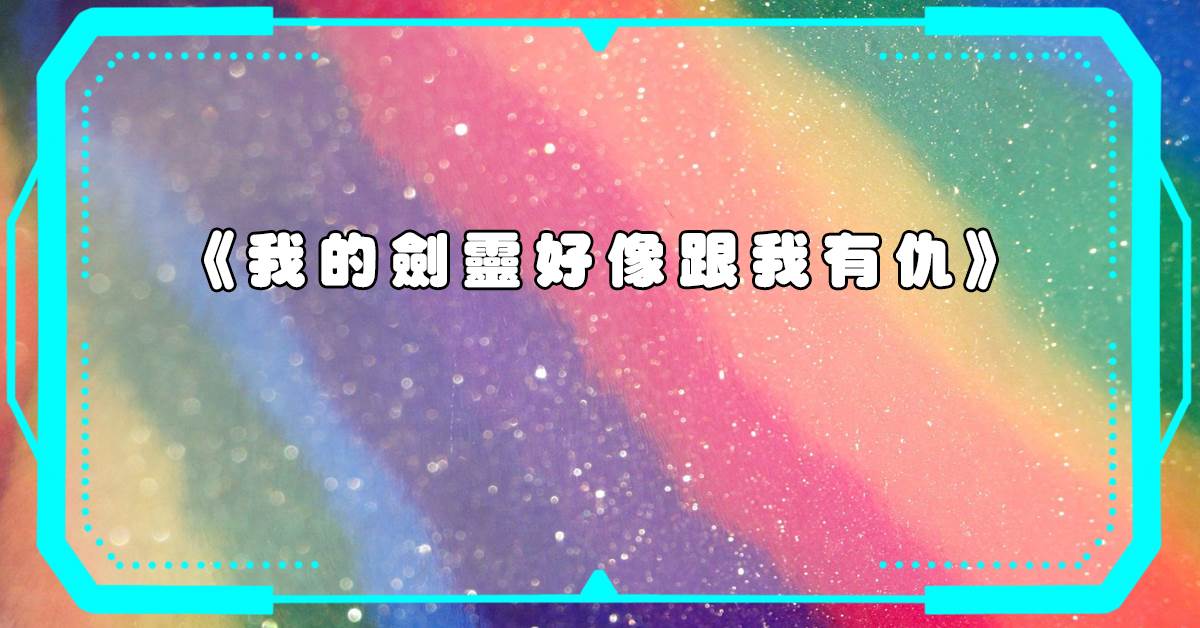《識玉/我的劍靈好像跟我有仇》第618章
“他們說是一回事,你怎麼說也是一回事。”領頭的魔修開口道,“那群墻頭草亂傳話的次數多了去。”
另一個魔修也點頭道:“你們道修前腳說合作,后腳便跟人翻臉的事情也多了去,我們如何信你們?”
“便憑我是白虎域域主。”秋白道,“我若是只是想殺你們,根本不必與你們費勁說這些。”
在魔修們將信將疑的目光中,秋白解釋著、
“可你也知曉,阻止魔修進入你們的領地,對我們并沒有什麼好處。”那領頭的魔修瞇了瞇眼,道,“甚至,我們會成為整個魔族的叛徒——盡管魔族并不團結,可他們卻不會放過可以踩我們一腳的理由與機會。”
“我知道,可我不正是為了這件事而來的嗎?”秋白耐著性子解釋道,“你們都應當知曉,他手上有那食夢蟲罷?”
一名魔修皺了皺眉,問道:“食夢蟲?”
秋白還有些驚訝,“怎麼,倒序之間都快傳爛了的事情,你們還沒有知曉麼?”
幾個魔修面面相覷,似乎都在對方的臉上看到了迷茫。
秋白這才意識到,這魔修的不團結,幾乎是體現在方方面面的。他們極少互相交流,就連極為簡單的消息,都需要流傳許久,才能叫整個魔域都知曉。
這也叫他們不能夠第一時間知曉道修那邊的事情。
因此,看向秋白的眼中多了幾分警惕,因為那食夢蟲對于他們而言,是完全陌生的東西。
“你莫不是隨口編了些什麼,便想蒙騙我等?”領頭的魔修開口有些不客氣,“我等雖然實力不如閣下,但是也不是任人指使的傻子。”
“我非是看不起閣下。
”秋白強自按捺著心頭的情緒,若是換做旁的魔修,他早就不與這些人廢話了,可就是這些魔修,是他們唯一的希望。
因此,即便心頭再不耐,他都還是需要耐著性子、一字一句地與這些魔修講清楚道理。
“食夢蟲是最開始出現在碧華閣之中的蠱蟲,然而流火尊卻是將其改造,成為了能夠控制人神志與行為、甚至在頃刻間將人變成血餌的蠱蟲。”秋白道,“而這些血餌,卻是流火尊實力的關鍵——你等即便不想與道修合作,可削弱流火尊實力的事情,你們應當也不會拒絕罷?”
他不敢與這些魔修戲說這血餌的用途,因為他怕這些魔修自己也心生邪念。
對于他來說,他是為了解決流火尊這個問題,而不是創造出更多的問題。
“這麼說來,這不是你們道修的東西?”一個魔修嗤笑了一聲,“怎麼,你們自己都控制不住,還來指望我們呢?”
秋白咬了咬牙,才將罵人的沖動忍了下去,“這蠱蟲已經被流火尊改變了,它不但能夠控制道修,連魔修都能夠控制。”
“哈!你不會以為魔修都像你們道修這麼多管閑事,還有那什麼所謂的同胞之情罷?”一個魔修大笑一聲,“要我說,那都是無用的東西——你快些省省力氣罷。”
“那蠱蟲近乎透明,極難察覺。”秋白面無表情地道,“若是我不提示你們幾位,閣下恐怕只會以為那是普通的爬蟲。”
“而它們若是要控制人也極為簡單,只要在你睡夢中成功進入你的夢境,你便被控制住了。”秋白繼續說著,“迄今為止,還未曾發現過什麼修為的修士是能夠不叫食夢蟲入侵的。
”
那些魔修都收斂了笑容,轉而瞪著他,“道修,你莫以為這樣就能唬住我們!”
光是聽著這個描述,他們便自腳底升起一股無與倫比的熟悉涼意。這等手法……他們當真是熟悉得很。
像極了他們那個不擇手段、從來都不會失敗的師父。
“我非是想要如何。”秋白淡淡地道,“我是在給各位一個活命的機會。流火尊的手段,既然諸位從他座下逃了出來,自然是非常清楚的。”
而這也說到了那幾個魔修的痛處,他們面色有些難看,面面相覷。
“除了我能夠與你們合作以外,我也不全是不給你們好處。”秋白道,“諸位若是能夠相助,在諸位不進入道修領地的前提下,我五百年內都不會對諸位動手。”
作為白虎域域主,秋白確實有這個底氣說出這般堪稱狂傲的話來。
早在他身上出現血孽之前,監兵便時常不在白虎域,而白虎域卻能夠出奇地安定。
究其原因,全都是因為那時候的監兵甚至會跨過界河,將在界河對面挑釁的魔修殺死。而不論是進入魔域還是離開魔域的路上,他不論遇到什麼魔修,無一活口。
甚至,有時候監兵心情好了,便去魔域尋幾個魔修助助興,心情不好了,又去尋幾個魔修尋開心。不論如何,不少魔族都被監兵不問青紅皂白地拿去開了刀。
可以說,戰神監兵之名,絕大多數都是用魔修的尸骨堆積起來的。
就連他們這幾個魔修,也對監兵的殺名頗有耳聞,畢竟,這放在魔族之中,監兵乃是能夠止小兒夜啼的存在。
這個承諾,對于他們來說,無異于保命符。不過是不去接近道修領地而已,他們身處在魔域的最西方,是在魔域的邊緣,本來前去道修領地便有著極遠的距離,更別說他們如今的修為,在道修那處討不著好,更無法輕易突破那防護陣法。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