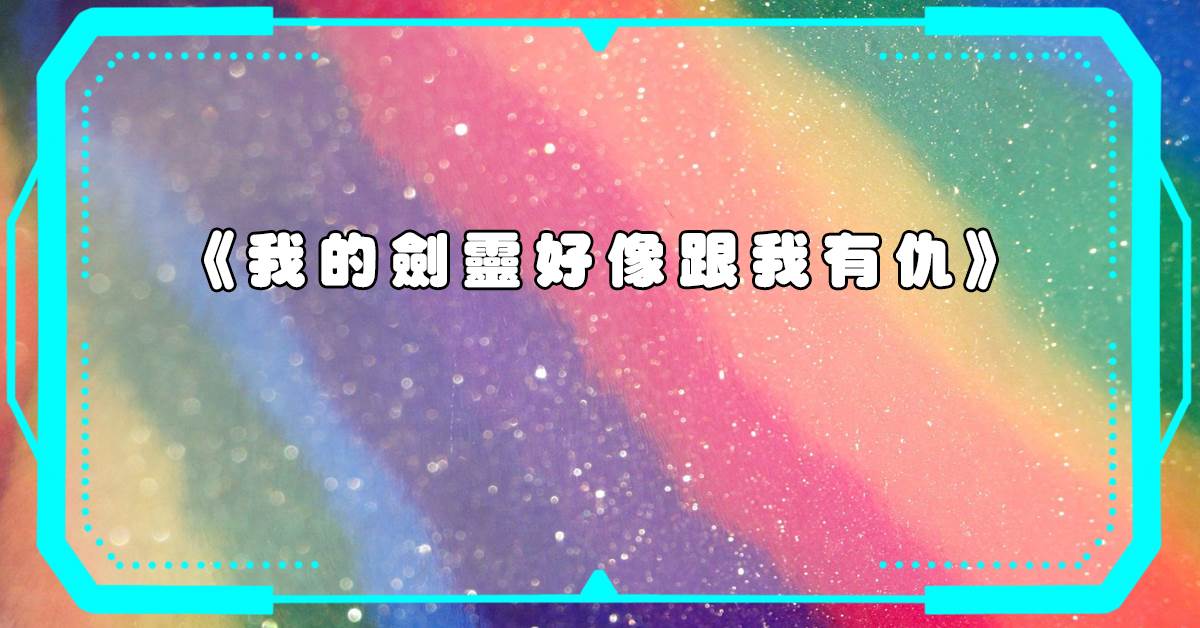《識玉/我的劍靈好像跟我有仇》第488章
鬼王生前是一個國家的帝王,在他死后,集結了自己生前的子民,想要在這處鬼域安家。可他們如何是那些習慣殺戮的鬼修的對手,他們初入鬼道,毫無還手之力,不少人都被旁的鬼修吞噬了,叫他們始終惶惶不可終日。
蘇長觀恰好在這時出現了,他原本只是驅逐那些圍繞在他身邊作亂的鬼修,順帶著趕走了在鬼王與他的臣民身側鬧騰的鬼修,無意之間救了他們的命。
于是,雙方便這麼認識了。
蘇長觀憐憫他們初初變成鬼修,卻在這鬼域之中毫無自保之力,念著曾經是同胞的情分,想要幫上一把。那時身上還帶著幾個東澤留給他的陣盤,便挑了個防護陣法的陣法留給他們,讓他們得以避免其他的鬼修的騷擾,得以在此處安身立命。
于是,蘇長觀便成了這座鬼城的救命恩人。
蘇長觀也得以在這鬼域之中有了一個落腳點,可以在鬼域之中嘗試將朗月明喚回。
只可惜,鬼王并沒有在朗月明身上察覺到一絲半點魂魄曾經存在的痕跡。換言之,便是連這鬼王也束手無策。
求助鬼王無果,蘇長觀又想著,當初孟昀應當是與些修為高深的鬼修做的交易,那些鬼修在鬼道上的造詣更深,浸淫鬼道的時間定然比初入鬼道而連自保之力都還未有的鬼王要久。因此,他病急亂投機醫,竟是帶了朗月明的身體去了那些先前被他趕跑的鬼修那處求助。
他也是走投無路了,而那些鬼修都極為記仇,記得是蘇長觀才導致他們失去了原來的領地,因而不肯出手相助,甚至還試圖侵占朗月明的尸體,以圖借尸還魂。
然而,即便那些鬼修說的話再難聽,蘇長觀也明白,無論是他們還是鬼王,已經無力回天了。他們都無法在朗月明的尸體當中,察覺到哪怕一絲朗月明的魂魄,他如今才意識到,朗月明恐怕已經魂飛魄散了。
可他還是不死心,非要自己想出個辦法來,于是絞盡腦汁在這鬼城之中,嘗試了各種辦法。
然而效果卻不盡人意。甚至,在他一次不注意的時候,那些被他趕走的鬼修,趁機闖入了這鬼王的宮殿,強行附在了朗月明的身體上。
那鬼修得了身體,肆無忌憚得驅使著朗月明的身體。蘇長觀始終顧忌著那是朗月明,不敢下狠手。于是竟被那鬼修一路橫沖直撞,幾乎拆了半個皇宮。
盡管鬼王那時候已經想盡了些辦法,卻也無法強行將那個占領了朗月明身體的鬼修驅逐出去,因為那多少會傷到朗月明的身體。于是二人最終只得想了個辦法,將朗月明的身體用特殊方法禁錮起來,封在這鬼城之中。
因著有鬼修附上朗月明的身體,因此她的身體不再能輕易帶出去,只得長年累月在此地接受鬼氣的侵蝕。
說完這些,鬼王面上卻露出幾分喜色,“近日來,我們想辦法引了些魔氣過來,魔氣與鬼氣兩相抵消之下,她的身體的異變延緩了不少。”
而出乎他預料地,蘇長觀面上卻沒有他預想的喜色。
蘇長觀沉默了片刻,也不知在想什麼,半晌,他抬起頭嘆了口氣,“那讓我過去看看她。”
鬼王自然無不應。
三人跟隨著鬼王進入到后宮的一處地窖之中。
幾乎是一走入這地窖,便能察覺到此處淤積的濃郁鬼氣。地窖地勢比較低,加上昏暗潮濕,更加適合鬼氣的沉積。
這處的地上畫著許多個陣法,有聚攏鬼氣的,也有聚攏魔氣的。而朗月明則處在地窖的最中心之處,被玄冰制成的鐵鏈束縛著手腳,安置在一口冰棺之中。
這般畫面著實有些詭異,沉睡在冰棺之中的人竟是還要戴著冰鐐銬。
這冰鐐銬之中凝聚了魔氣,壓制著這處的鬼氣,叫這占據了朗月明身體的鬼修即便蘇醒也無法輕易動彈。
鬼王解釋著:“若是那鬼修醒來,定是要大發雷霆的。可我們怕她傷到這副軀殼,只得出此下策。”
蘇長觀點了點頭,“無妨,你們也有難處。”
步驚川走上前去,卻見到朗月明如今已經和前世所見的模樣大相徑庭。
原本他這次也做足了準備,知曉朗月明如今模樣會與先前活著那時截然不同,可當他真的看到的時候,卻還是因為眼前所見震驚得無以復加。
朗月明原本白凈的面上透著一片死寂的青灰,面上與手腳上皆浮現出黑紫色的血管,就連她的皮下,也出現了不少的淡紫色瘀痕,仿若丑陋的尸斑。就連她的的唇上也變得干癟,變成了死氣沉沉的絳紫色。
她的顴骨高聳,整個人干枯而又瘦弱,皮膚也開始有些發皺,若非蘇長觀肯定,步驚川完全不會知曉這是朗月明的身體。
他這才意識到,蘇長觀先前所言的“面目全非”是什麼意思。
盡管如今的朗月明也是一身紅衣,可光是看著這冰棺之中的人,步驚川怎麼也無法將眼前這個干枯得如同一句干尸的女子,與曾經那個張揚肆意的紅衣劍修聯系到一起。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