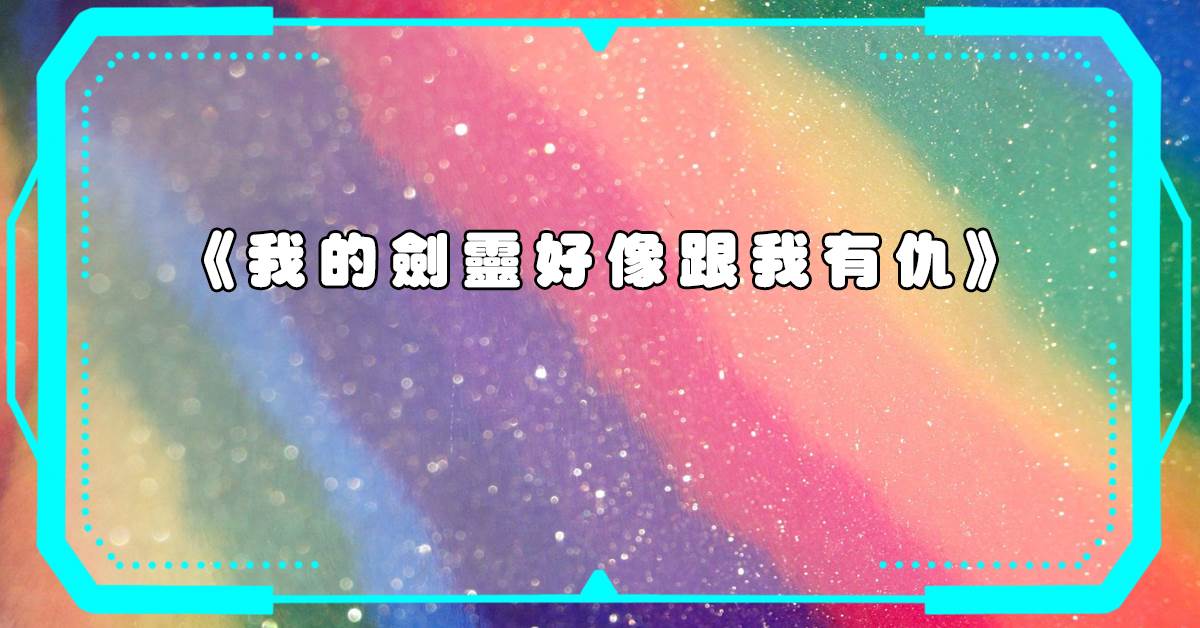《識玉/我的劍靈好像跟我有仇》第353章
從秋白抱著他的雙臂與緊貼著他的胸膛,他察覺到秋白的僵硬。
秋白似乎組織了許久的語言,才終于想起來自己該說些什麼:“你……”
東澤對于步驚川的記憶極為模糊,他蘇醒過來的時間太短,還未來得及仔細查看步驚川的記憶,因此他也不知道,二人之間,竟還有這樣一番過往。
不受東澤控制的身體微微朝著秋白的方向靠近,他附在秋白耳邊,輕聲道:“秋白,我心悅你。”
不等秋白回答,他又接著道:“或許你不知曉,我自很久之前,便幻想與你并肩,亦想過將你護在身后。”
秋白沉默許久,神色變換數回,才終于開口道:“……你待凡人,不也是如此?”
只是秋白此刻的嗓音沙啞,想來心底里定然是不如他面上表現得那般鎮定。
他聞言抬起頭來,直視著秋白,聲音帶著些許的顫抖,道:“我只欲待你一人如此。”
秋白面上閃過幾分怔然,直直地看向他,仿佛失去了言語的能力。
東澤稍稍動了下指尖,發現軀殼的掌控權又重新回到了自己手上。他忽然醒悟過來,根據上一回的經驗來看,眼前的便是自己需要應對的劫數。
關于周途城的記憶對于東澤來說太過模糊,因此他也有些拿不準自己應當如何應對,于是他選擇按兵不動,仔細觀察著秋白的舉動。
秋白怔愣許久,別開了目光,“……現在不是說這個的時候。”
聽得秋白回答,東澤這才下意識地打量了一番自己眼下的處境。
身體的掌控權回到了他手上,此時五感仿佛是被秋白提醒了一般,在此刻緩緩地出現。
東澤感應了一番,發現自己如今身體的狀況已經不能更糟糕。
經脈被外力所摧殘,靈力在體內橫沖直撞,靈脈顯然是被強行撬開過,時不時地泄出些許靈氣,沖擊著他的身體,叫這具軀殼的情況雪上加霜。
若非那靈脈一直都護著他的心脈,這副軀殼恐怕隨時都會陷入萬劫不復的境地。
在這個要緊關頭,竟還能分神同秋白說出方才那些話語,即便是東澤,也不由得有些佩服自己。
那麼,在這般情境之下同秋白說這些話,秋白……同意了嗎?
東澤抬眸看向秋白,卻不經意間與秋白的視線撞到了一處。
秋白此刻望向他的眼中,神色頗為復雜。
猶豫、欣喜、擔憂、畏縮混雜在一處,幾乎是即刻叫他心疼起來。
東澤忽然便不想知曉結果了,他不想這般逼著秋白作出應答。
“……你是認真的嗎?”秋白忽然問道。
東澤一愣,還未反應過來秋白的意思,便聽到秋白又問了一句。
他思慮片刻,覺得即便是步驚川,也不會不靠譜到將這等話語當作兒戲,因此他點頭道:“自是真心所言。”
秋白目光中的波動更甚,卻再未言語。
東澤的一顆心如今被懸在此處,半落不落的,有些拿不準,卻不知自己該不該追問。
他心中隱約察覺到似乎有哪處不太對勁,然而卻不知是何處出了差錯。
心魔對此事的了解,恐怕比東澤自己更甚。他不敢露出分毫破綻,叫心魔察覺。
秋白又似乎是猶豫了許久,才開口道:“我不過是想同你確定一番……我始終覺得有些難以置信,你我之間,分明便不該有這種情誼。
”
秋白所言,叫東澤愣在原地。
為何秋白會這般說?是礙于他前世時對秋白說的話,秋白才會這般同一無所知的步驚川這般說麼?
可盡管東澤對于步驚川的記憶并不是十分熟悉,然而東澤卻十分清楚,后來的秋白,是答應了步驚川的。
可正是這一日?
他自是看得出來,秋白在此事上的糾結,然而他也拿不準,到底是秋白不愿答應步驚川,還是秋白礙于東澤曾經的警告,才會作此應答。
又或許是……秋白對他的情誼,在這千年的等待之中消耗殆盡,秋白對步驚川與東澤,再無多余的情感。這卻是東澤所不敢想的。
他前世的布置,不光是為了完成師父們的遺愿,更是為了……他與秋白的將來。他不顧一切地舍棄自己原本的軀殼,為的正是能夠與秋白毫無芥蒂地相處。
可若是秋白告訴他,自己對他再沒有半分情誼……
東澤定了定神。秋白應當不會是對他沒有半分情誼,在方才經歷雷劫前,秋白看向他時,目光之中的擔憂不似作假。
可,若那擔憂只是給步驚川的呢?秋白曾在東澤這邊受過挫折,可他現在也看到了,步驚川對秋白的執著。步驚川遍體鱗傷之際,卻也還是在這關頭,孤注一擲地表明了自己的心意。
一方是曾經傷過自己的存在,敬畏有加,卻遙不可及。另一方卻是一腔熱忱,不顧一切地接近。
秋白會選擇哪邊,不言而喻。
東澤回想起秋白見到自己時的神色,不由黯然。
他能夠以往日的威信,壓迫秋白道出違心的話語,然而不論再怎麼壓迫,他也無法改變秋白自己的想法。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