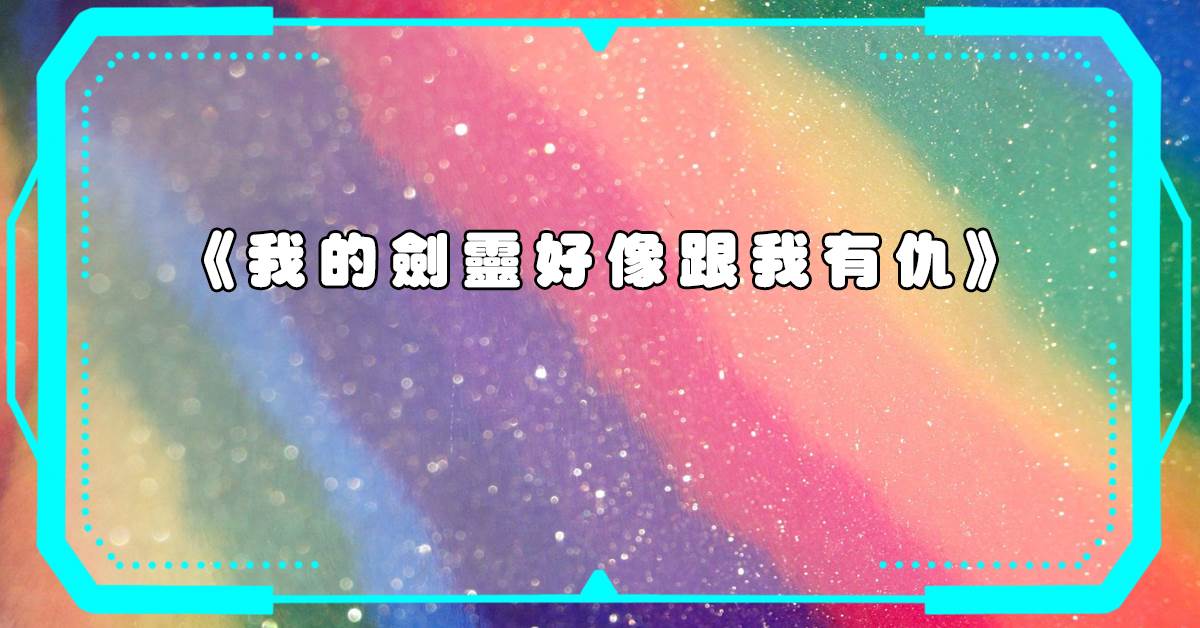《識玉/我的劍靈好像跟我有仇》第333章
秋白敏銳地察覺到了步驚川的不安,視線落到了步驚川身上,眉頭緊鎖。
“多謝夫人。”他見步驚川已經問完了,便在此時出來打圓場,“此處我們已經設下陣法,三月內能夠防住大部分魔修的襲擊,請夫人放心。”
婦人知曉這是結束對話的潛臺詞,她也沒有多問,只點了點頭,走向她的丈夫。
看著婦人的背影,步驚川忍不住出聲道:“抱歉,方才是我來遲了。”
他方才趕到之際,那男人早已生機斷絕,可他看那男人身體還溫熱著,想來也是剛過世不久。若是他能再早一些趕到,那麼這個男人至少不會……
婦人聞言,微微頓住了腳步,回過頭來看著他。婦人剛經歷過生死關頭,眼下還要面對亡夫之痛,已然擠不出笑容,然而她的眼中不見半點怨恨。
“我男人,不過是命不好罷了……你至少救下了我與孩子。”婦人低聲道,“小道長,你不必自責,你做到了你該做的。”
步驚川微怔,久久不能言語。秋白見狀,安靜地牽著步驚川的手離開了婦人的院子。
不論是東澤還是步驚川,都是偏涼的體質,此前秋白曾暗地里猜測這是因為東澤的本體是玉的緣故。
可轉念一想,步驚川乃是人胎孕育,有著肉體,應當不會受本體的影響。想來應當是些先天不足,才導致天生熱不起來。又或者是步驚川幼時曾被邪祟拿去一番折騰,那時候便有陰氣入體,才使得他天生畏寒。
不論如何,步驚川如今便生得這副怕冷體質。盡管修士不畏寒暑,然而步驚川卻是多多少少還有些畏寒。
本來天氣一冷,步驚川身子也會偏涼些,手腳更甚。當他長時間不動的時候,更是冰涼。
眼下秋白一摸步驚川的手,更是冰涼徹骨。
察覺到秋白的觸碰,步驚川緊握的手下意識松開了,秋白去握他的手,才發現他的手心已經全是冷汗。
好在此時潭池鎮情況趨于穩定,二人也已行至了不引人矚目之處,也能將話好好地敞開說一回。
“是阮尤的手筆。”步驚川開口道。
此地魔修的實力并不強,想來也是因為此處生活的都是凡人,用不著花費太大的力氣,因此才派出了這等實力弱小的魔修。
這些魔修在步驚川的火陣之下無處遁形,不多時便化為飛灰。
在步驚川出手之前,他已經觀察過一段時間。他并非貿然出手,畢竟他親身經歷過周途城被滅那一夜,自然知曉魔修實力不容小覷。然而在他觀察后,卻發現此處的魔修與周途城那時出現的魔修大相徑庭,就連他布下的最簡單的陣法都扛不住。
而這些魔修他先前便猜測像是傀儡,傀儡應當是受人驅使,而這些無法自主思考的傀儡魔修,竟只有實力最弱的部分留下來攻擊凡人,這背后定是有人在安排。
他不懼魔修實力高強,長衍宗的護宗大陣維系千年,扛過了不止多少大大小小的襲擊,若是同那些魔修對上,大不了他可以開啟靈脈拼死一戰。然而這些魔修出現的背后竟是另有人布置,這才是叫他暗暗心驚的。
他想起了太云門。
同樣都是有著護宗的陣法,如今陣道沒落,會解開陣法的修士并不多,而以蠻力破陣——陣法本便是用的以一敵十的原理,防的就是蠻力。
若是強行破陣,元嬰修士也未必能夠強行破開金丹修士布下的陣法。太云門本來能夠輕易抗下這等魔修的襲擊,可那本該護佑太云門的陣法,卻偏偏被人打開了。
這些跡象都叫他不由自主地想起了一人——阮尤。
除卻十四時在羅家村的一面,他其實再沒有見過阮尤。周途城那日的驚鴻一瞥,他也不敢確定那人真的是阮尤。
盡管他從周途城回去時,從江極的反應中看出那事與阮尤脫不了干系,可他卻始終無法肯定。
然而這數年來,阮尤雖未真正現身,卻如影隨形。阮尤好比一條毒蟲,在看不見的角落中潛伏著,只待著他走過之時,給予他致命一擊。
這種感覺叫步驚川心中無端生出一股暴躁,只想將這蜷縮在暗處的毒蟲從陰影之中揪出,把這惱人的毒蟲撕碎。
他與阮尤的血海深仇,也該做個了結……
他忽然一頓。伸手輕輕捏了下眉心,他還未回到長衍宗,也并不能確切知曉阮尤做了何事,為何如今便斷定是血海深仇了?
仿佛有一段不屬于他的情緒闖入了他的認知之中,有些隱約的記憶與印象,叫他失了自己原本的判斷。
或許這只是不祥的預感。他這麼想著,強迫自己將心頭的情緒壓下。
他方才說得篤定,便是因為他確實在線索之間發現是阮尤的手筆。可阮尤與他有過節一事又從何而來?此事他并沒有依據,卻自然而然這般想了,這才是他自己覺得莫名的地方。
而秋白卻不會懷疑他說的話。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