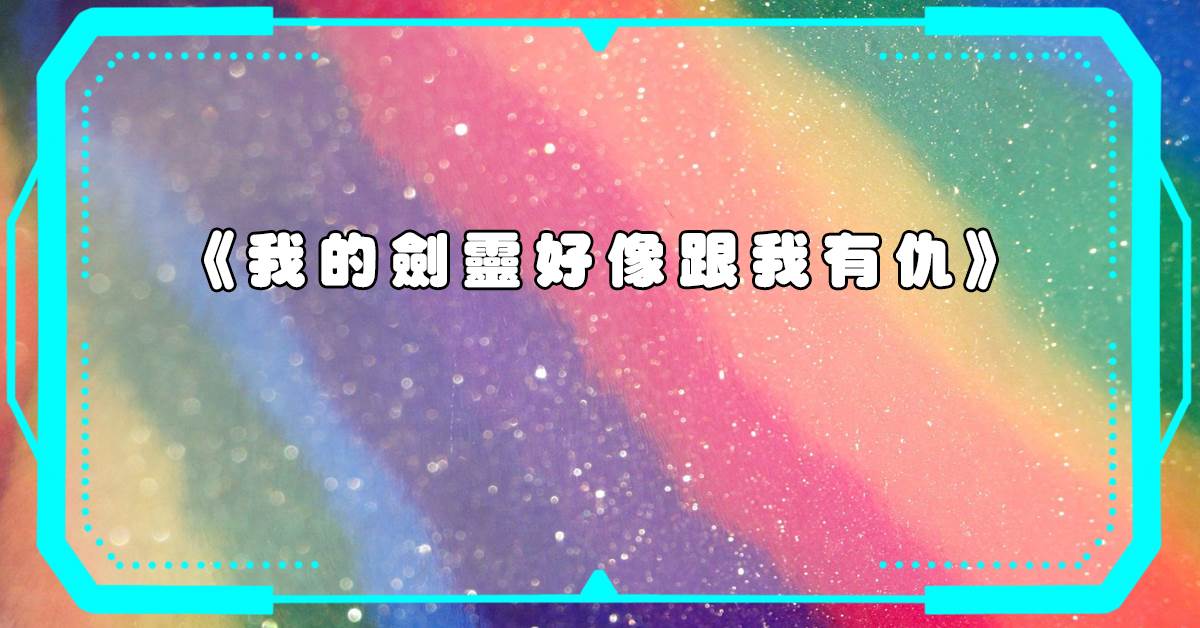《識玉/我的劍靈好像跟我有仇》第313章
想來是這二人交流時用了些傳音入密的法子,叫步驚川連聽都未聽得只言片語。
他本以為那只是太云門長老內的普通交流,不想讓他這個外宗人聽到罷了。然而,在下一刻那兩位長老投到他身上的目光,叫他明白了此事似乎沒有這麼簡單。
“你是何人?”那位后來的長老率先開口問道。
不待步驚川回答,宋怡便開口道:“步小友乃是步驚川,師從長衍宗,擅陣法施布——方才正是得力于步小友的鼎力相助,護宗大陣方才得以再度開啟。”
誰知,聽得這句話,二位長老卻不約而同地皺起了眉頭。
肖長老沉思片刻,拂了拂衣袖,道:“什麼長衍宗——我從未聽說過,這人,可靠嗎?”
步驚川聽得心頭生出幾分不爽。肖長老這般倨傲,說話間雖是談及他,卻連個正眼都沒有,擺明了便是要給他一個下馬威。
更何況,前不久才在太云門中舉辦了折桂大會,長衍宗此回雖成績不出眾,卻也是到了太云門參與折桂大會的。這肖長老說不知曉長衍宗,不止是給了步驚川下馬威,更是給了整個長衍宗一巴掌。
另一個長老適時道:“不過是些上不了臺面的小宗門,也不知道他們的辦法是否可靠。”
“二位若是有什麼話想說,不妨直說。”步驚川抿了抿唇,他如今心性雖有長進,然而對于這等不善的話語,且涉及到他出身的宗門,他還是有些忍不住了,“不必在此處貶低了我,再去貶低我出身的宗門。”
盡管知曉這二人在他面前說這番話語,定是別有目的,然而步驚川還是忍不住同這二人置氣——無論這二人抱有何種居心,都不該這般說他出身的長衍宗!
肖長老嗤笑一聲,道:“此處乃是太云門,哪有你一個外人說話的地方。”
另一位長老也補充道:“也是怪宋怡,竟連外宗人都敢隨意相信。如今竟是連云石都給外人接觸,也不止是安的何種居心。”
“云石之上的護宗大陣,乃是太云門之根基,事關一宗安全。”肖長老搖了搖頭,“擅自將宗門陣法交于他人之手,罔顧大局,女子果然不為我所用。”
二人這般一唱一和,饒是步驚川,也多少看出了些不對勁來了。
這二位長老的惡意,并非只針對他,而是他身后的宋怡。這二人,只不過是借著踩他,來落了宋怡面子罷了。
此回宋怡同他一道修復了云石,扭轉了太云門在對戰魔修之時的劣勢,定然會在太云門之中被人提及。這兩位長老恐怕是因為有著不可告人的目的,才在這節骨眼上想將宋怡敲打一番。
想通這其中關竅,步驚川也冷靜下來,還想著說靜觀其變,看看這二人葫蘆里賣的什麼藥。
誰知,一直未出聲的于任凌卻忽然道:“你們這般憑空捏造,污我師尊與外宗友人清白,便不臉紅麼?”
方才二位長老說話期間,無人敢插嘴,四下安靜得很。于任凌聲音清朗,一開口便登時吸引了在場眾人的注意力。
兩名長老見是他,面上那囂張神色褪去幾分,肖長老皺眉道:“你怎的跟著你師尊久了,開始替些外宗人說話?”
“師尊教養我多年,授予我許多道理。”于任凌死死盯著他們二人,“其中一條便是,不得信口開河。”
“步道友雖是外宗人,然而大敵當前,你二人可曾看清自己的敵人在何處?”于任凌越說越氣,聲音也不由得拔高了幾分,“你們如今不止辱我師尊,還辱志同道合的道友,不知二位居心何在,可看得清這大局?”
他拿這兩位長老自己的話來刺這二人,令得這二人面色也難看起來。
一旁,又有一位長老適時出聲勸導:“此事確實是宋怡做得不對……”
“我師尊哪里做得不對了?”于任凌猛地回頭,打斷了那長老的話,“修補陣法,維護大陣運轉,保護太云門安寧——她哪里做錯了?”
有一位長老小聲嘀咕著:“一介女流,修行便是錯。”
那位出聲勸架的長老裝作沒聽見這話,只道:“無論怎麼說她也不該讓一個外宗人接觸我們的護山大陣……”
“那你還有什麼辦法嗎?”于任凌冷道,“除了修補陣法,你還有別的更好的辦法嗎?莫非你要眼睜睜看著太云門弟子與那些魔修死斗,最后體力不支全數喪命麼?!”
于任凌方才一直都護佑在宋怡跟前,為的就是防止她在修補陣法之時被魔修襲擊。他的消耗并不大,方才能夠好好地站在此處。然而更多的太云門弟子,修為薄弱,已然扛不住如潮水般的魔修,在陣法生效后,直接一屁股坐在地上,喘著粗氣。
如今看去,不少弟子已經受了傷,如若陣法不及時生效,恐怕……便不是受傷這麼簡單了。
“你們一直在指責我師尊,非是因為她所作所為有何缺陷,而僅僅是因為她身為女子。”于任凌道,“不是麼?”
于任凌一番話噎得那幾位長老說不出話來,又被說中了心思,幾位長老鐵青著臉,不再吭聲。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