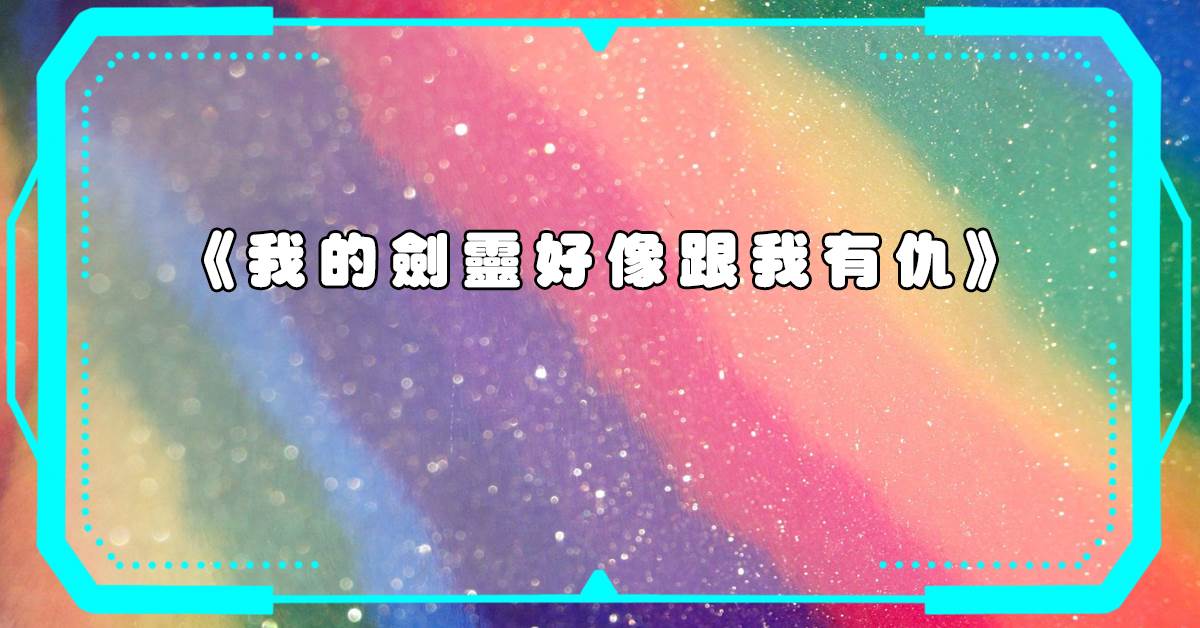《識玉/我的劍靈好像跟我有仇》第189章
這時候他自己才意識到,自己這次或許比先前喝的,還要多得多。
至少他前幾次喝多,也不至于這麼狼狽。還是說是因為他知道秋白在此處,他才敢如此放肆?
步驚川看向秋白。此時秋白正低頭替他看著腳下的路,沒有注意到他的目光。
他卻感到前所未有地安心。
有秋白在他身邊,他可以放心地將自己交給秋白,即使看不見腳下,他也不會感到茫然與恐懼。
步維行與岑清聞,自幼教導他的便是自立自強,不能依靠他人。然而他或許自很久之前,便開始有意無意地依靠秋白。
縱使他明白在許多事上,他只能依靠自己,但也不妨礙他偶爾貪戀一回秋白的可靠。
他唯有在秋白跟前,才能真正地放松。
秋白將他攙進屋中,又問道:“那你現在自己還清醒嗎?”
步驚川乖巧地點點頭。
“我同你打了熱水,”秋白說著,朝身后的地上一指,“你自己洗個臉,換身干凈衣服,就去睡覺。”
步驚川聞言,為了表示自己喝醉并沒有影響到自己反應能力,迅速起身朝著秋白所指的方向走去。
秋白說這處放了盆水……
腳上傳來溫暖濕潤的感覺,步驚川慢半拍地低下了頭,便見到自己一只腳踏進了水盆中。
為什麼這處會放盛了水的水盆?
費力想了半天,腦海中才靈光一閃,想起來方才的事。
哦,是秋白放在此處的。
一想到秋白,他心感不妙,竭力擺出一副無辜神色轉過身去,正好看到努力壓抑怒火的秋白。
他一見秋白這神色,心知自己做錯了事,又迅速將踩進木盆的腳收回來。
他注意力都放在秋白身上,沒注意到隨著他收腳的動作,木盆被帶倒,水跡洇了一地。
他抿了抿唇,低聲道:“我、我不是故意的。”
又見秋白神色沒有緩和的跡象,還遲遲不說話,連忙彎下腰摸索,想將水盆端到外邊,嘴上還不住道:“我去換一盆水……”
當步驚川拾起木盆后,才注意到一地的水跡,他忽然意識到秋白正是因為這事生氣。他猛地直起腰,想要向秋白檢討一番自己的錯誤,卻沒注意到一旁的桌子,額角猛地在桌角上撞了一下。
額角處的疼痛襲來,步驚川下意識伸手去捂額角,手中一松,手中的木盆因為這一下變故,沒有抓準,一下子從手中滑了出去。僅剩的一點水,便“嘩——”一下灑得滿地都是。
木盆在地上滾了兩圈,又如砧板上的魚垂死掙扎般掙動了幾下,便再不動彈。
對上秋白幾乎都要冒火的目光,步驚川此刻覺得自己才是那條砧板上的魚。
“放著,讓我來。”秋白終于忍無可忍地出聲,快步上前,將他按在床上坐下。
步驚川便依他所言,乖乖坐下,任由秋白將他外衫和鞋襪除去。
秋白似是故意冷落他,將地上的水跡收拾完畢后才坐到他旁邊,替他按摩額角的傷處。
這點傷比起他先前受的傷輕了不知道多少,就連疤都不會留,即使放著不管,頂多就是第二日有些瘀血罷了。
饒是如此,秋白仍是處理得十分細心。
秋白的靈力并不能助他療傷,卻能疏通這個傷處的血管,使得第二天瘀血不至于太厲害——也不至于那麼疼。
然而,秋白手上的力道卻不輕,似乎含了點怒意在里頭,想要在這小小一個腫包上發泄殆盡。
步驚川被秋白按得生疼,卻又不敢出聲抗議,只能縮著脖子任其動作。好在秋白也只有開頭那幾下用了些勁,后續也放輕了動作,令得步驚川暗暗松了一口氣。
那腫包并不大,不一會兒秋白便道:“好了。”
說罷,秋白直起身子后退一步,拾起木盆后轉了個身,只給步驚川留下一個背影。
這背影步驚川見得多了,每回秋白要回到金素劍中時,便是這般的背影。原本司空見慣的場景,卻令得他心頭陡然掀起一陣恐慌。
許是酒壯慫人膽,步驚川忽然伸手拉住了秋白。
他只用指尖輕輕地拉住了秋白的袖口,秋白只要稍稍使上些力,便能掙脫。
秋白腳步一頓,沒急著掙開,只微微回頭看向步驚川,用眼神朝他要一個解釋。
步驚川在他的目光之下,卯足了力氣,輕聲道:“今晚留在外面,好嗎?”
秋白眼神一動,步驚川見有戲,拉著他袖口的手便晃了晃,微微拖長了聲音喊他:“秋白……”
小時候他同步維行與岑清聞撒嬌,便慣喜歡用這套,加上那時候他還是整個長衍宗最小的弟子,莫說他師父師娘二人,長衍宗的長老和師兄師姐們都遷就著他,這招可謂是屢試不爽。只不過后來逐漸長大,他也生了些許羞恥心,不再向人撒嬌。
只不過這一次,他忽然腦中熱血上涌,便拽住了秋白的衣角。他看著秋白怔楞的神色,心中對他這般反應頗有些不安,便又將手中的衣角晃了晃。
秋白久久地看著他,就在他覺得需要再做點什麼的時候,秋白輕嘆一聲。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