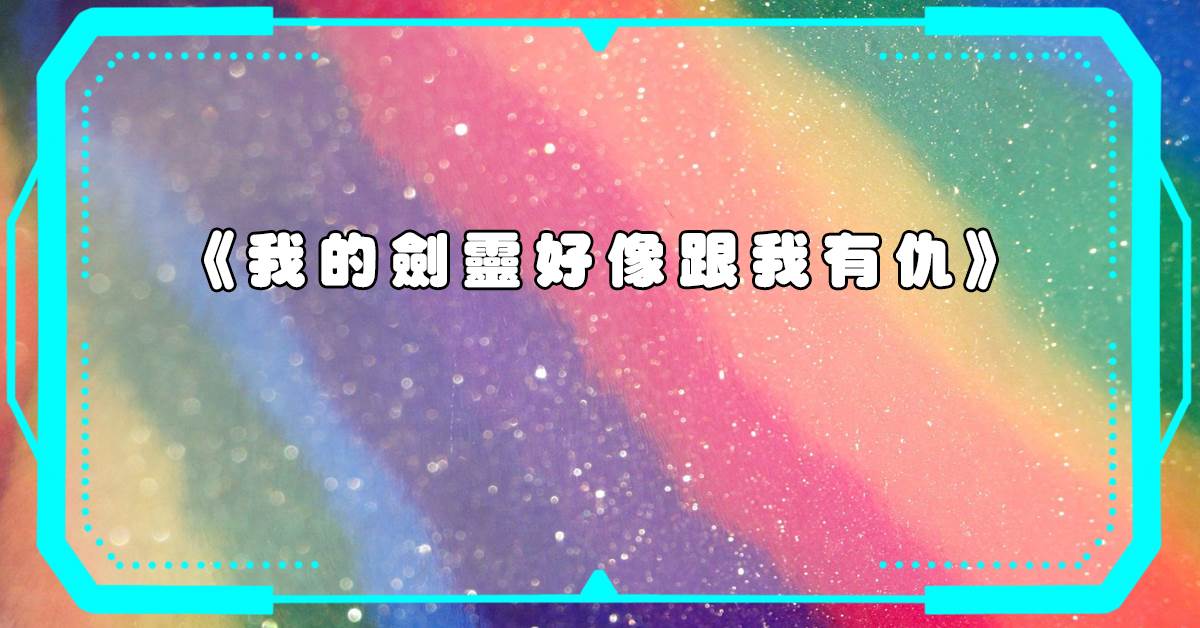《識玉/我的劍靈好像跟我有仇》第69章
修真界長年以來,眾人都習慣了弱肉強食,強者欺負弱者,向來便無幾人會在意。樊易仗著宗門背景與自身實力給他們下馬威,在修真界中還算不得多大的事。
更重要的是,他們還未有為自己討回顏面的能力,因此樊易才敢在掌門與步維行的眼皮子底下這般肆無忌憚。
被人看輕的感覺著實難受,他輾轉數次,白日時出現的畫面卻始終揮之不去。
他輕嘆一聲,最后又翻了個身,面向床外。
剛想閉上眼強制自己入睡,可借著昏暗的光線,他似乎看到了房中有什麼東西與白天不同了。
他眨了眨眼,剛剛升起的困倦之意便被這個新的發現驅除殆盡。他抬起頭,猛然對上一雙清冷的雙眸,才意識到是秋白站在了他的床前。
是了,他平時靈劍向來不會離身,為數不多離身的時候,也就只有他睡覺的時候。每天睡覺,他便會解下腰間的劍,放在床頭,確保金素劍不會離他過遠。
他方才翻來覆去的模樣,恐怕便這樣被秋白看得一清二楚了。
面上后知后覺地發燙,意識到自己方才那番丟人的表現,步驚川拿不準秋白心中所想,只拿一雙眼睛瞅著他,等秋白主動開口。
“你大半夜的不睡覺,這是在做什麼?”秋白主動問道。
“無事,我認床……”步驚川一張嘴便后悔了。
原因無他,這個理由太過蹩腳,連他自己都信不過。
光線太暗,他看不清秋白的表情如何,只是聽到他的尾音微微上揚,似是帶了幾分威脅的意味,“真的只是認床?若只是這樣,我便先回去了……”
“等、等等!”步驚川下意識地伸手拉住秋白的衣襟,又極快地意識到自己方才說了什麼,極力為自己辯解著,“認床,認床只是其中一方面!我、我還有別的……”
聽他開口,似是終于見到威脅有了些許成效,秋白輕輕地舒了口氣。他撩起衣擺,在床沿處坐下,道:“愿聞其詳。”
秋白這麼一副洗耳恭聽的模樣,步驚川心中卻又生出些遲疑。他覺得自己的想法羞于啟齒,同時又不知該如何去表達,一時間,陷入了兩難。
可秋白格外地有耐心,一直靜靜等著他開口。
“我……我……”步驚川糾結了許久,終于開口吐出第一個音節,他一咬牙,心一橫,決心將自己此刻的顧慮同秋白說個清楚,“我在想樊易。”
“你想他做什麼?”秋白問道。
步驚川悶悶道:“無非便是為了過幾日的弟子比試,我在想,我若是遇上了同他路數相同的弟子,該要如何。”
其實他真正想問的是,若是他碰到了樊易,他該如何是好?
但實際上,他與樊易相差了一個境界,若是正常比試,他是對不上的。可他心中的憂慮卻又壓不下去,如今疏雨劍閣有一個樊易,日后若是出去闖蕩,他更是會遇到千千萬萬的樊易,屆時每回都要受這麼一回氣,他不甘心。
可不甘心也沒用,他實力不強,樊易想贏他自是輕而易舉。別說樊易,就連一般的疏雨劍閣弟子,他都不是對手。
所幸秋白似乎讀出了他言語之間的未盡之意,問道:“你可是在擔心,過幾日的弟子比試?”
步驚川點了點頭,又礙于此時屋中未點燈,光線昏暗,他擔心秋白看不到,于是便道:“是。
”
秋白又問:“你在憂心這弟子比試的何事?”
步驚川低聲道:“疏雨劍閣的弟子身經百戰,無論是身法的變換多變,亦或是當機立斷的能力,都比我強上許多。我這般貿然與他們對上,與我而言,似乎太難實現了。”
“你不去試試,你如何知道行或不行?”秋白道,“你總歸需要與這些人接觸,方才知曉會是何等差距。”
“可我……”步驚川咽了口唾沫,想起先前看著樊易與星移對戰,那種壓倒性的優勢,令他在臺下光是看著,也想不出半點對策來。他只知道,若是當時與樊易對上是自己,恐怕會比星移狼狽十倍、百倍。
“我不行,”承認這一點令他格外地泄氣,聲音都不由得低落了幾分,他深知自己的無用,因而也痛恨自己的無能,“我或許這輩子,都無法與星移師兄那般游刃有余。”
星移是長衍宗百年來天賦最出眾的弟子,可就連星移都在樊易手下討不得好,那更別說他了。
“你不需做到像誰那般,你只需要做你自己。”秋白輕聲道,“若是你想做,那便去做。這世間,不會有你做不成的事。”
直視著步驚川迷茫的雙眼,秋白又補充道:“行或不行,在事情未發生前便不會有定數,唯有傾盡全力,方才能求得一個結果。”
步驚川愣在原地。
從未有人同他說過這般的話,更不會有人同他說,這世間沒有他做不成的事。就連步維行,也是一再同他強調說,凡事莫要強求。
這還是他第一次從旁人口中聽得對自己的期待,令得他知道,他也能被人期待。
半晌,待到心緒平復大半,步驚川才顫聲應道:“好,我定當全力而為。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