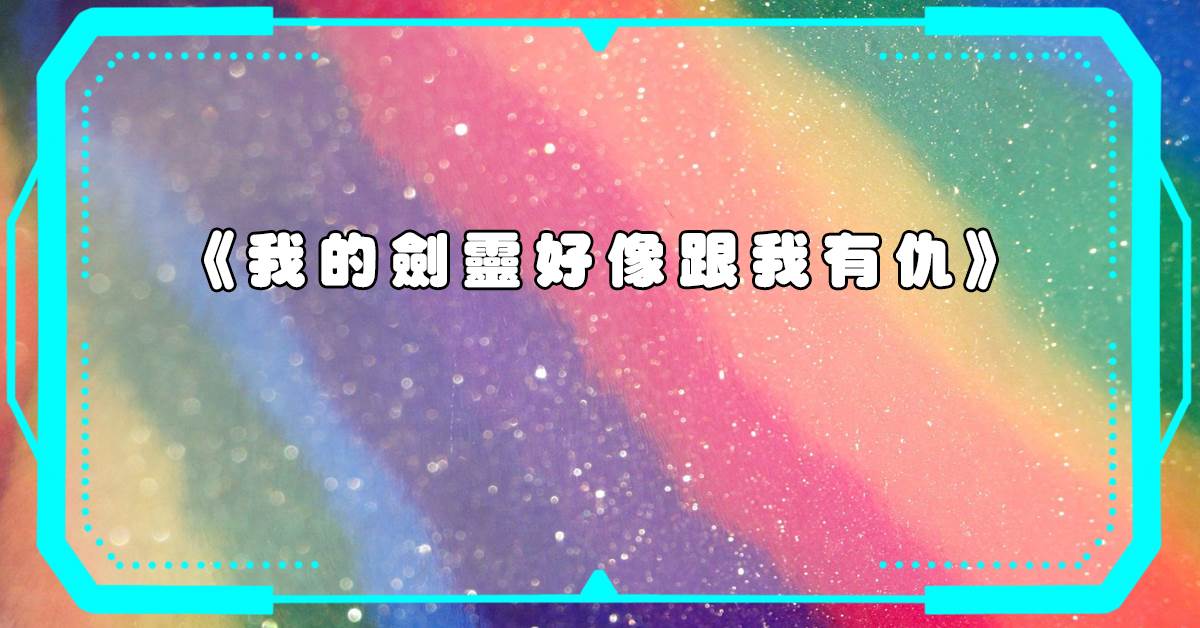《識玉/我的劍靈好像跟我有仇》第37章
步驚川低頭看著自己,自己身上分明還是完好如初,方才的感觸似乎只是他的錯覺。
婦人仍是高聲道:“那只是祛除邪祟的手段,仙師與我說過!”
步維行“嘖”了一聲,似乎忍耐得格外辛苦。他對這婦人的胡攪蠻纏極為無奈,又不好發作。
“夫人,”星移適時地出聲解圍,“這其中或許還有什麼誤會。”
婦人猛一轉頭,怒瞪的雙目看向星移,像是剛發現他站在那似的,將他上上下下打量了好幾回。
“你們,是一起的?”婦人面色的神色忽而一轉,從驚怒變為祈求,“那你能不能告訴我,我兒現在在哪?”
星移被這話問得一怔,還不待他回答,那婦人面上的臉色又驟變,“你也不想告訴我?”
束手無策,星移求助的目光轉向步維行,步維行便出聲替他解圍,說出的話卻驚到了在場的人。
步維行道:“他便在此處。”
“他在?”婦人怔愣半晌,轉而看向站在面前的眾人。
疏雨劍閣的弟子,早在發現婦人的矛頭只是對著長衍宗時,便躲得遠遠的,以防引火燒身。現在站在婦人跟前的,只有一眾長衍宗眾人。
她的目光在五人當中梭巡半晌,步驚川是四位弟子當中年紀最小的,她的目光便自然而然落到了步驚川身上。
恰好,步驚川目光也停留在她身上,二人的視線便這般對上了。
“我兒,”婦人喃喃著,“是你,是你嗎?”
婦人上前數步,眼見著馬上就要走到步驚川跟前,步驚川后退了一步,將二人之間拉近的距離拉大了。
像是被步驚川這動作驚醒了,婦人忽然反應過來,驚疑問道:“你,你在躲我?”
步驚川垂下眼,不去看婦人的臉。
關于身世,步維行從未瞞過他,在他懂事后,他便知曉了自己是師父養子。而自己的身世,他卻是一無所知。
步維行對他的父母只字不提,他自己對此事,說不好奇是假的。
他自然是對自己的父母也存過幻想,而長大了一些后,雖不再幻想,卻也會在不為人知的時候,去想象自己的父母是何種人。
而方才在婦人同步維行爭吵時,他隱約想起了一些事情。
他的父母聽信來路不明的醫師的話,在他身上試過放血、扎針,以至于他后來一見到那位醫師便哭。
醫師說是因為他身上的邪祟害怕自己,因此父母對此事從不在意。只有他自己看到了從醫師身上冒出的森森鬼氣。
最后他們將他置于曠野,不顧此時是寒冬臘月,天寒地凍。因為醫師說想要驅除邪祟,須得在天氣最冷的時候引寒氣入體,才好對邪祟下手。
地上野獸橫行,天上鷲鷹梭巡。
但凡有半點變數,這些東西隨時都能要了他的命,可他們一心只想將他體內不存在的“邪祟”驅除。
他的父親拉著母親,母親尚且有幾分猶豫,父親便道:“若是他死了,那邪祟也會消失。若是沒死,我們的兒子便救回來了,何樂而不為?”
男人用從醫師處學來的話寬慰母親,二人便這樣放下心來。
二人消失在曠野之中,因為醫師說,驅除邪祟須得借天地之力,此時不宜有人在場,他的父母信以為真,頭也不回地離開。
醫師在他們離去后才現身,卻不是為了驅除所謂的邪祟,因為醫師自己,才是最大的邪祟。
最終這只邪祟被及時趕來的步維行斬于劍下,步驚川因此而得救。
他當著村民與步驚川父母的面,斬下那半鬼的頭顱,在四下逸散的鬼氣之中,帶走了步驚川。
無一人阻止,就連出聲阻撓的都沒有。
也不知是不是那一次被暴露在曠野中連襁褓都曾未穿的原因,步驚川自小便格外畏寒,直至現在也未見好轉。
前塵往事一并想起,步驚川的眼角有些發澀,他眨了眨眼,“可明明是你們那時候,不要我了。”
“那是因為我那時候一直沒有反應過來,”婦人語氣中帶了幾分安慰的意思,“再說,那只是為了驅除你身上的邪祟,你如今身上沒有邪祟了,不是很好嗎?”
婦人語氣轉而變得急切,“我兒,你能理解我的,是嗎?”
“可我要是說,我身上壓根沒有邪祟呢?”步驚川道。
“你這說的什麼話,”婦人道,“那時候仙師說,你的眼睛便是邪祟作亂的跡象,他都已經幫你將邪祟驅逐了……”
步驚川的眼睛自小便異于常人,天生便剔透如琥珀,在陽光照射下還會有金光流轉。小時候還有許多師兄師姐會圍過來,好奇地打量他的眼睛。
這般顏色出現在哪都不奇怪,但偏生出現在一屆凡人子女身上,便透著十分的妖異,這也成了他被懷疑的開始。
“你再看清楚,”步驚川抬起眼瞼,“我根本不是什麼邪祟,我的眼睛天生如此。”
“但那時候,放血、針扎、火烤,甚至還將我赤身裸體置于野外,這便是你說的‘仙師’替我驅邪?”步驚川道,“你可曾知道我那時候的感受?”
這一句話便將婦人問住了,她怔愣半晌,眼睫劇烈顫抖,眼見著就要落下淚來。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