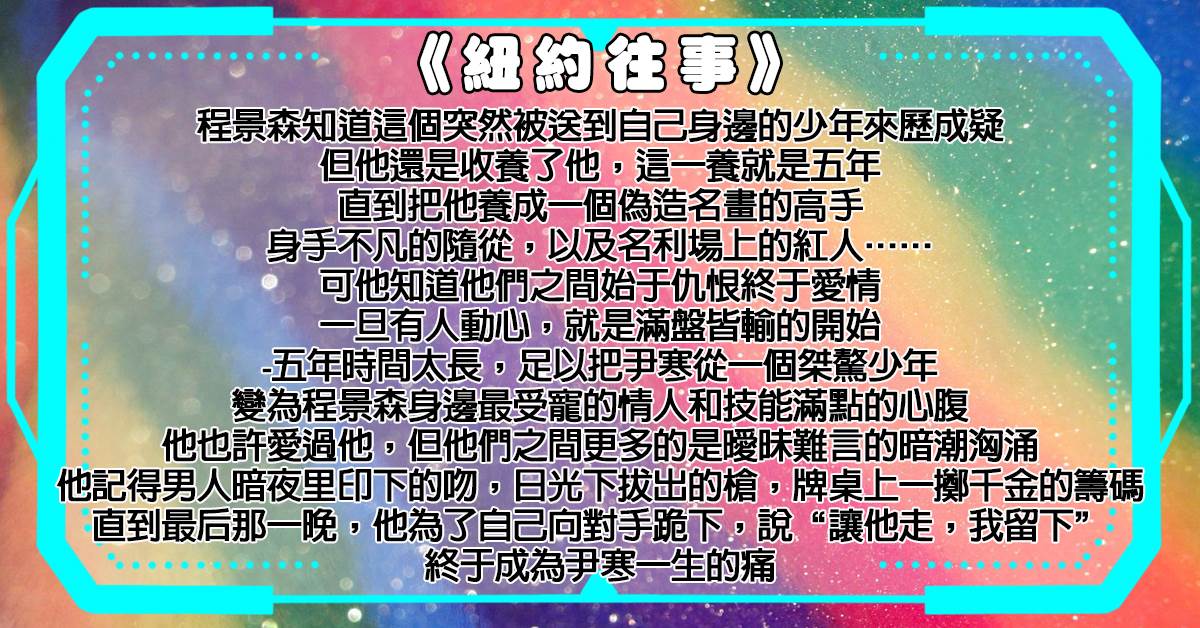《紐約往事》第49章
程景森沒再說話,把他放在床上,轉而問他,“早餐想吃什麼?”尹寒順從地說,“有什麼就吃什麼吧。”
徐媽和瑪姬都不在,程景森給他端了滿滿一盤的食物,牛奶酸奶、可頌、培根卷、藍莓醬、松露醬......都是他平日喜歡的口味。
他也不嫌多,接過托盤枕在腿上,慢慢地吃。
他坐在靠近床邊的位置,從這個角度,視線穿過臥室門可以看到一點書房里的情景。
程景森有時轉動皮椅,他那筆挺寬闊的背脊就會進入尹寒的視野。
高燒仍未退去,少年身上傷痕累累,面色卻很平靜。
他用藍莓醬涂抹可頌,送進嘴里咀嚼,雙眼卻一直望著書房的方向。
吃完可頌以后他擦了擦手,摸到自己左耳的那只黑石耳墜。
痛。
傷口還沒愈合,耳墜也頗有重量,所以一碰就痛。
這已經是他身上第二個關于程景森的印痕了。
紋身、耳洞和耳墜,他想,程景森對他應該是有幾分感情的,否則不會宣示表示所有權。
而自己呢?自己是什麼感覺。
尹寒此前從沒談過戀愛,程景森從里到外開發了他,也是他心里一顆萌發的開端。
昨晚的經歷很奇異,先是一個人對另一個人袒露了自己最不堪回首的過去,然后轉變為一場近乎虐待的性愛。
尹寒想,自己對于男人的仇恨,竟沒有因此而加深,反而變得更加復雜難解——這是動心的表現嗎?程景森再次走進來,他與他視線相交。
兩個人都很平常,仿佛昨晚的一切只是做了一場夢。
程景森看到那杯牛奶已經喝完了,問他,“再給你一杯奶?”尹寒靈光一閃,突然對他說,“上周學校體檢,我長高了兩厘米,現在是177了。
”
程景森似乎愣了一下。
他表面看來只是沉默地走到尹寒跟前,心里卻想,這小孩如果是對自己攻心,那這一招真是太高級了。
他養了他快有半年,折騰了他整整一夜,現在他不但不氣不鬧,乖乖坐在床上忍著高燒吃早飯,還仰起頭來對自己說長高了兩厘米,用那張眉目清雅優美的臉。
——試問誰能受得了?程景森的理智未及深思,手已經伸出去,在尹寒下頜處輕輕捏了一把。
少年垂下眼,把那只空玻璃杯遞過去,“那就再要一杯吧。”
程景森接過杯子的同時,沒有馬上離開,問他,“不想被我轉手賣掉?”尹寒點頭。
“還想幫我找回吉澤爾的遺作和骨灰?”尹寒又點頭。
“昨晚的道歉呢?”尹寒說,“都是真的。
我知道錯了。”
男人嘆了一口氣,“小寒,我該怎麼相信你?”-尹寒被程景森關在臥室里過了三天。
唯一的活動空間就是臥室和盥洗室這兩處連通的套房。
三天的禁閉足夠讓人把很多事情想清楚。
直到這時尹寒才意識到,或許并不是因為自己有多麼誘惑動人,而是程景森愿意給他特權恃寵而驕。
那一夜的瘋狂纏綿仿佛讓程景森把對他的感情都用盡了。
男人不再碰他也不再吻他。
對于他提議的尋找吉澤爾骨灰和遺作一事,也沒有任何回應。
昨天早上醒來時,他能感受到男人的晨勃,那根硬挺的性器抵著他的腿。
他本來想為他口,卻被程景森直接推開——在這之前他從來沒有推開過他。
尹寒第一次感到無措。
他關在房間里胡思亂想過了一整天。
直到很晚程景森也沒有進屋休息,尹寒抱著靠枕坐在沙發里捱到深夜十一點。
窗外的私家車道傳來流動的光亮,尹寒快步起來,走到窗邊,看見程景森領著一個身材火辣的女人從商務車里走下。
尹寒整個人都傻了,從自己生日以后程景森沒再碰過別人。
他在窗臺邊立了很久,人影散去,車也開遠了,花園里只剩一片重疊迷障的樹影。
他倒回床上,幾乎一夜未眠。
清早程景森給他端早飯,見到他眼下的一圈青黑,伸手摸了一下他的額頭,很冷淡地說,“燒退了。”
尹寒看著他,“我有按時吃藥。”
頓了頓,又道,“病已經好了,程先生想做什麼都可以。”
——暗示的意味已經很明顯。
程景森心里一扎,尹寒從來沒有在自己面前表現得如此主動。
過去他所做到的頂多只是乖順聽話。
不管自己要求什麼,少年不反抗也不拒絕,任憑擺布。
可是從兩天前開始,他似乎學會了對自己投懷送抱,那種又生澀又勾人的樣子實在讓程景森難以自持。
是因為想繼續留在自己身邊復仇嗎?還是擔心在羽翼未豐時被轉給下家從此斷了生路?程景森感到前所未有的煩躁。
昨晚那個女人他沒碰,對方撩了他半個小時,他毫無性致,最后給了錢打發走了,然后獨自在客臥床上睡了一個囫圇覺。
凌晨五點時處于半夢半醒的邊緣,他下意識伸手去撈人,少年光滑微涼的身體不在觸及范圍內,他就此醒來。
他清楚自己對尹寒的感情已經越界。
這樣下去太危險。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