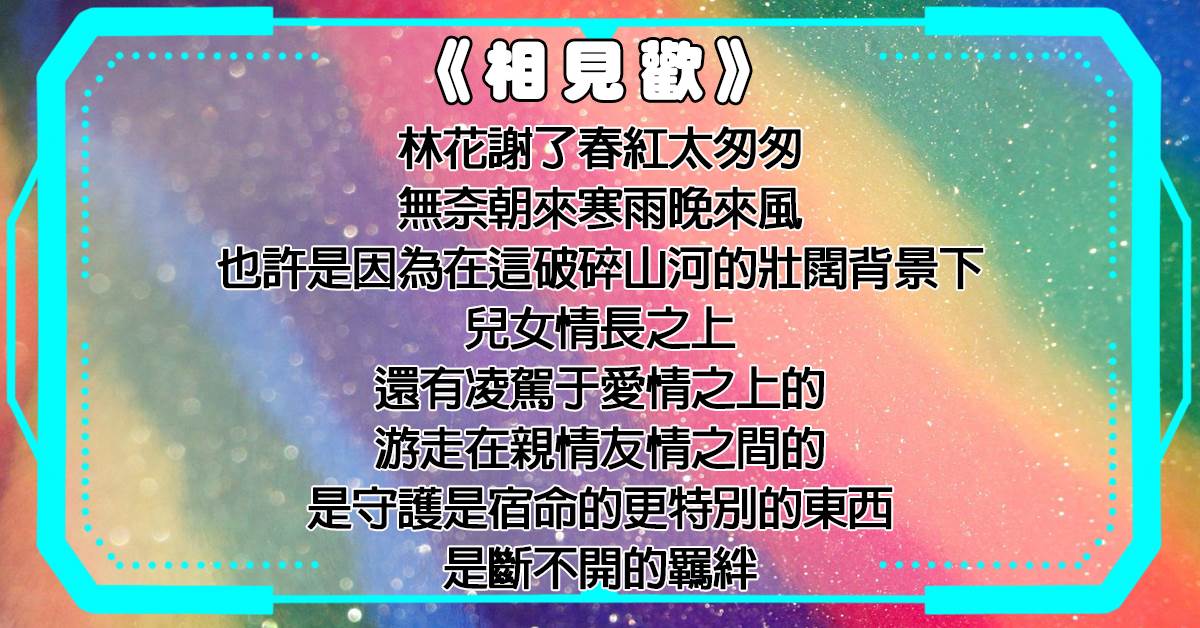《《相見歡》》第372章
“那麼,你就只能自己回去了。”費宏德說。
武獨神色一變,段嶺尋思良久,不得不承認費宏德的話永遠都是簡簡單單就能道出真相。
“你說得對,費宏德先生。”段嶺答道,“我確實打算回去,但我需要查清楚一個方向。”
段嶺相信李衍秋,卻不敢完全把希望寄托在李衍秋身上,他已經嘗試過一次完全地信任了,但無論怎麼樣,總感覺人,是斗不過老天的。置身于命運的漩渦之中,他必須有所為,否則事后想起,一切就只剩下遺憾了。
“就這樣吧。”段嶺伸了個懶腰,打了個呵欠,吩咐昌流君先下去休息,說,“這段日子里,我需要時間來調查,以防出現任何可能的變故。”
段嶺不再提接下來的計劃,武獨也沒有多問。
北方的春天來得很晚,整個漫長的一月里,冰雪都沒有化,但年初三一過,段嶺便吩咐下去,需要推行新政。姚復派出的商隊來了,與河北互通有無,帶來了種子。
武獨則帶兵去,將附近的山寨掃蕩了一番,曾經傳說河北山匪肆虐,但現在看來也就那樣。山中的青壯年大多在河間城活動,上一次幾乎全被秦瀧帶走,前去行刺李衍秋。
這次段嶺并沒有去特地追究什麼,畢竟原本的山寨中只剩下不足兩千的老弱婦孺,段嶺便讓武獨帶下來,安置在河間城。愿許配的許配,不愿許配的便自己過日子去。
雪化春耕的那天,南方的信來了,是一名黑甲軍士兵親自送來的,里頭是謝宥的親筆信。
段嶺并不清楚謝宥是否知道自己的身份,也許只是李衍秋交代他前去調查,但可以肯定的是,謝宥已經知道李衍秋準備對付牧曠達了。
信里面是關于上一次段嶺詢問的昌流君的身世,謝宥以黑甲軍的關系網調查,確有此事。其中各個輩分的孫家族人,段嶺特地召來昌流君,一一問過,昌流君都能答上來。
這不可能是事先調查了背好的,畢竟牧曠達派昌流君出來行刺,誰也不會想到昌流君會特地來投奔段嶺。
謝宥的來信更告知,牧曠達與曾經的西川孫家毫無交集,也未曾派人去取閱過孫家的資料。這樣一來,段嶺終于能放下心,把解藥交給昌流君。
“我們什麼時候回去?”昌流君看著解藥,問,“要動身了?”
“還沒有。”段嶺說,“只是給你解去毒。”
昌流君說:“一朝沒了武功,倒也少了煩心事。”
說是這麼說,段嶺卻知道昌流君更牽掛南方。
“忍著吧。”段嶺說,“如果你敢私自動身走掉,就別怪我了。”
昌流君忙道沒有,既然效忠了,自然就不會再回頭。然而段嶺也心知肚明,昌流君多多少少有點擔心,擔心真到了求情的時候,段嶺能不能幫牧磬脫罪。
“你就別嘮叨了。”武獨被昌流君念叨得耳朵起繭子,說,“怎麼這麼啰嗦?”、昌流君三番兩次,找武獨確認,王山一定能救牧磬,陛下十分器重王山,因為他有過救駕之功……武獨已經對他十分不耐煩了。
一元復始,萬象更新。正月十五到了,二月二也來了,及至上巳節那天,潯水畔一群鄴城軍單身漢在河邊求偶,各個赤著上身,一時間河里盡是年輕的健碩男人的肉體,簡直令段嶺不忍卒睹。
“有什麼好看的!”武獨說,“不要看了。
”
當兵的個個肌肉分明,段嶺忍不住多瞥兩眼,便被武獨騎著馬帶走了。
“已經三月了。”段嶺泡在溫泉里,說,“江州還沒有任何動靜。”
“你急著回去?”武獨問。
“昌流君急。”段嶺說,“我看他只是有點坐不住。”
武獨答道:“你要相信你四叔。”
段嶺心里的不安全感越來越強烈,就像當年在上京等候一般,但按道理說有鄭彥跟在李衍秋身邊,應該不會出什麼事才對。
但那年,也有武獨跟在李漸鴻的身邊。
段嶺收攝心神,知道無論怎麼樣,這都將是自己與武獨在河北過的最后一年了。四月里,南方傳來不少消息,朝廷擢升起用一批年輕有為的官員,又是一年的用人之月,功曹考核,各地都在朝中央送信,由江州點選考校。
麥田一片綠油油的,夏風吹了起來。
林運齊找到在城外巡視的段嶺,朝段嶺說:“太守大人,得述職了,今天朝廷來了人。還有一應考核之事,都得由您安排。”
段嶺擦了下手,問:“來人是誰?”
“三郡巡司使黃大人。”林運齊答道,“河南、河北、山東三地俱是他負責。是你同門。”
段嶺馬上就朝城里跑,黃堅正在府中與施戚說話,詢問鄴城財政,段嶺便歡呼一聲沖進來,與黃堅撲在一起。
“老師怎麼樣?”段嶺笑道。
“已有快一月沒去拜見他了。”黃堅先讓段嶺坐定,也不客氣,自顧自笑著替他斟茶,顯然沒把自己當客人,又說:“大伙兒都讓我過來,好好看看你。”
同一年舉仕的,只有段嶺未敘誼,點了探花就匆匆忙忙走馬上任,如今想起,竟也只認得離開江州那天夜里吃的一碗面與幾名進士,當即寒暄一番。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