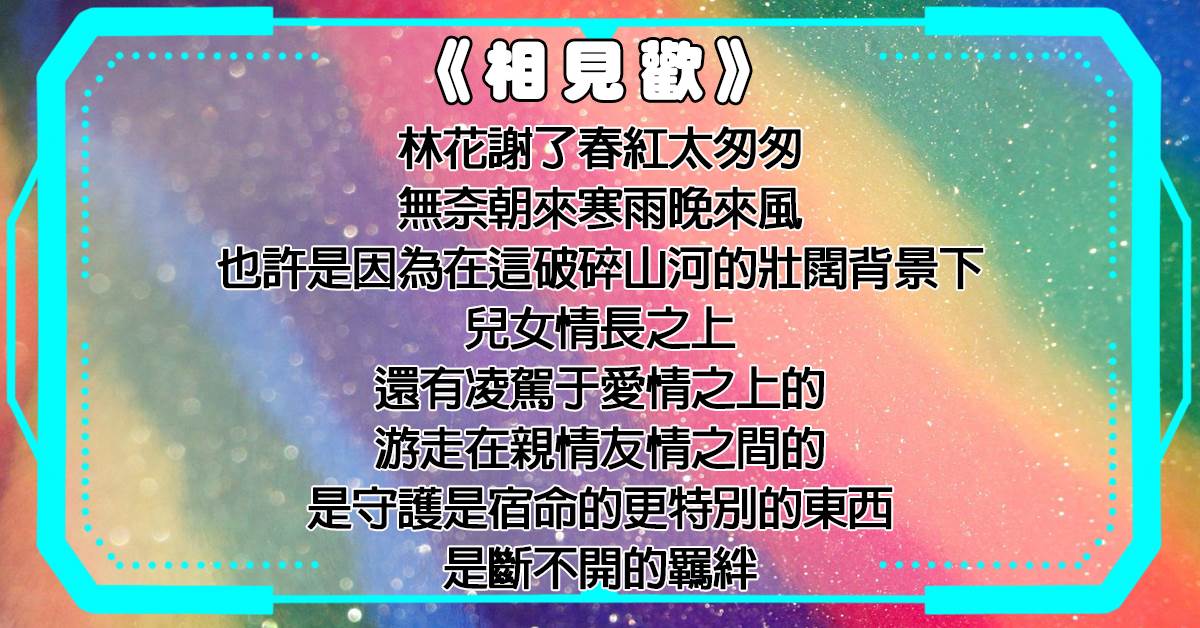《《相見歡》》第231章
”
段嶺便推門出去,雖然只有短短的幾句對話,不知為什麼,心里卻異常平靜,這次正式的見面,仿佛讓他安定下來。叔父與父親,這兩兄弟仿佛都有著奇異的本事,無論天翻地覆,都能淡然視之,跟在他們的身邊,哪怕天塌下來,也絲毫不懼。
武獨與段嶺對視,便推門進去。段嶺在外頭等著,看了鄭彥一眼,鄭彥卻若有所思,抬頭看著廊下滴落的水滴。段嶺一顆心都在御書房中的武獨身上,聽見李衍秋的聲音不大,仿佛在交代什麼,武獨只偶爾低聲答“是”。這次的談話未持續多久,李衍秋便道:“你退下吧。”
武獨這才出來,朝鄭彥略一點頭,帶著段嶺離開。
“他問了你什麼?”段嶺問。
武獨站在廊下,抖開蓑衣,給段嶺穿上,答道:“他問我,是否找到了鎮山河的線索……”
突然間武獨止住了話頭,剎那轉頭,發現了什麼。
“走。”武獨說。
武獨牽起段嶺的手,與他一步跨出御花園后,幾步轉入皇宮,進入兩座建筑中的狹縫里,時而讓段嶺走在他身側,時而讓段嶺走到他身后,又不時回頭看兩側墻壁高處。
這一次連段嶺也看見了,一個身影從隔墻頂閃過。
出宮時,暴雨的積水已沒到了奔霄膝蓋處,武獨先讓段嶺上馬,調轉馬頭,以背脊擋住宮墻高處對后宮門墻壁的射程。
“駕!”武獨一抖馬韁,奔霄在水中穿行,如一艘劃破黑暗,通往彼岸的船。
相府依舊燈火通明,回來的第一天便發生了這麼多事,兩人濕淋淋地回到家里,水已經漫到房里來了,今天一整天都沒在家,段嶺本來打著瞌睡,一看這模樣,瞬間就精神了。
奔霄在馬廄里沒地方趴,也不能睡覺,只好站著。
武獨上前清理案上的行李,段嶺問:“剛剛跟蹤咱們的是什麼人?”
“影隊的。”武獨答道,“膽子太大了,要不是下雨天,又與你在一起,定要教他們好看。”
段嶺知道蔡閆已經開始設法對付自己了,今天只是跟蹤,也許是為了探他們的虛實,接下來說不定要采取明目張膽的手段。
“陛下朝你說了什麼?”武獨問。
段嶺答道:“什麼也沒有說,只是約略問了幾句,不清不楚的。”
段嶺告知武獨經過,又問:“后來你們在書房里說了什麼?”
“他說。”武獨答道,“他忽然改變主意了。”
“什麼?!”段嶺詫異道。
武獨又說:“讓我該做什麼,依舊做什麼,既不想入東宮,便依舊陪著你,他會幫我解決。過得幾天,待水患結后,他說,還有事情派給我。我猜還是讓我找鎮山河。”
“有線索了麼?”段嶺問。
武獨搖頭:“所以我問你在御書房中,與他說了什麼話。”
“我沒說什麼啊。”段嶺皺眉道。
“那就奇怪了。”武獨上前兩手提起床榻,朝段嶺說,“把磚頭墊床腳下,架高了晚上好睡覺。”
段嶺墊起一張搖搖欲墜的床,平生第一次碰上發大水,也不知道怎麼辦,只得與武獨坐在床上,不敢亂動,生怕床掉進水里去。
“我困了。”段嶺說。
“睡吧。”武獨說,“晚上當心點,別動。”
段嶺哭笑不得,只得小心躺下。
“明天怎麼辦?”
段嶺抱著武獨,倚在他的肩前,喃喃道。
他的人生充滿了未知與兇險,牧曠達、李衍秋、蔡閆……許多事,許多人,組成一張錯綜復雜的網,令他不得解脫,牽一發而動全身。
要朝牧曠達交代,要提防蔡閆的算計,要向李衍秋證明自己的身份,如此多的難題橫亙在面前,猶如一堵堵墻,難以撼動。
“什麼都不要想。”武獨說,“睡吧。”
翌日清晨,太陽照進來時,暴雨已經停了,江州卻依舊漫著水。不僅江州,就連城外的長江,也已水位高漲。
“起床了!”武獨朝房里喊道。
段嶺睜開眼,看見床前搭著木板,底下墊著磚,直連到院里的照壁后,拐了個彎出門去,像個小小的碼頭。
段嶺便笑了起來,日上三竿,武獨不知道什麼時候不聲不響地做了這麼多事。他穿上外袍,束好腰帶,小心翼翼地沿著木板走去。大門外,橫著一條小船,船上生了個爐子,正在煮開水。
段嶺坐在船中,武獨便給他梳頭,系發,說:“帶你玩去,走嘍——”
“等等等!”段嶺昨夜的煩惱都被拋到了腦后,忽然靈光一閃,有了主意。
這是百年難得一遇的洪水,發生在遷都后的第一年開春,實在是不祥之兆。城中議論紛紛,人心惶惶。皇宮建在高地,倒是無恙。
蔡閆清晨起來時,第一件事就是傳馮鐸,聽完稟報后,一臉怒容。
“他在御書房內待了多久?”蔡閆問道。
“不到一盞茶時間。”馮鐸答道,“后來兒郎們還想再跟,被武獨發現了,只得先撤回來。”
“卷子呢?”蔡閆顫聲道。
“還在御書房中。”馮鐸說,“陛下已經看過了,殿下,如今不管再做什麼,都再無用了。昨夜陛下傳令,命國子監通宵達旦判卷,今日初晨開始評錄。理由是洪水泛濫,不得再耽擱。今天下午就會張榜,后天召集殿試。
”
“這麼快?!”蔡閆難以置信道。
馮鐸說:“待得殿試后,再要下手,就是誅殺……誅殺朝廷命官了,殿下?”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