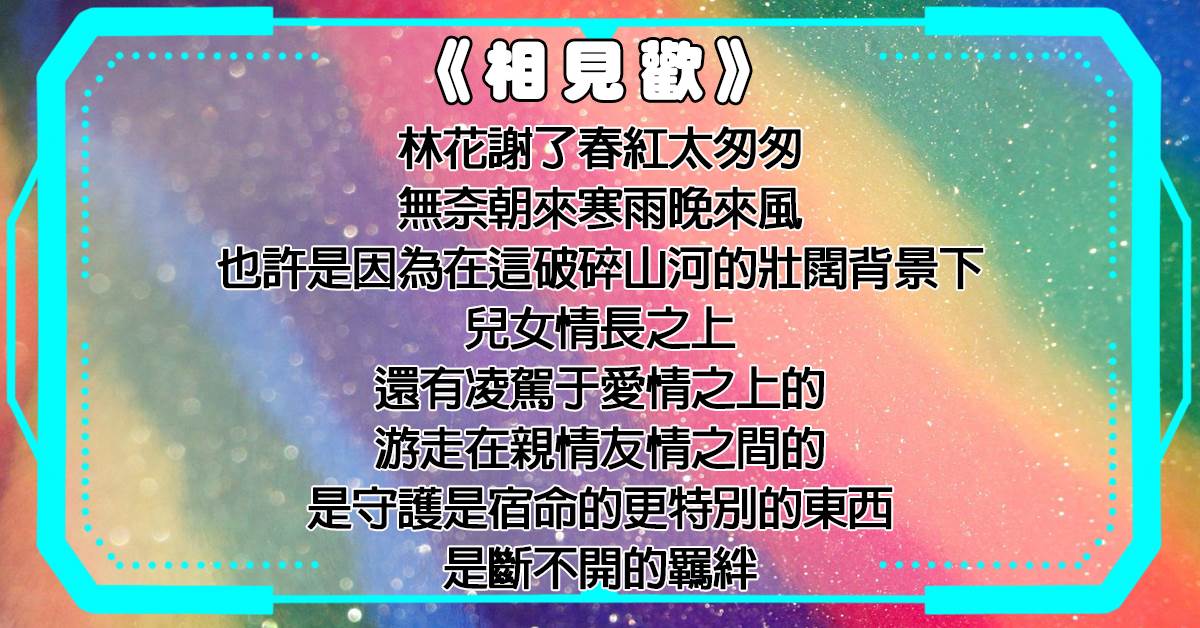《《相見歡》》第218章
”
牧曠達喚了聲長聘,說:“去書閣里將布兒赤金拔都上一次送的信取來看看。”段嶺心中怦怦地跳,又寫了第二張,將兩張并作一張,說:“第二張也是拔都親筆,寫的是議盟,這一張記不清楚了。”
寫完后長聘已把另一封信箋取來,放在牧曠達面前,牧曠達對著看了眼,說:“確實是元人王子的口吻。”
段嶺又過了一關,心里松了口氣。長聘隨意一瞥,笑道:“你這字跡倒是與他有二三分像。”
昔年拔都學寫漢字,念書做文章,大半都是段嶺所教。段嶺這才發現這點,說:“真的嗎?”
段嶺取來信箋,細細地看,看到拔都熟悉的字,語法仍出現了不少錯誤,只覺既好笑又熟悉,不禁生出思念之心,百般滋味,涌上心頭。
“布兒赤金拔都從小便在上京長大。”長聘說,“這倒不會有假,想必是學到漢文,奇赤又不會讀書識字,將祖宗的元文忘了,會說不會寫,凡事都以漢文傳書。”
“我倒是覺得。”牧曠達看了一會兒段嶺寫下的信,說,“極有可能是拔都不愿讓族中旁的人知曉,以免走漏風聲,令事情脫離控制,于是用漢文寫信予阿木古與哈丹巴特爾。”
段嶺心里十分感激牧曠達,竟然把自己的謊給圓了回來。
“也罷。”牧曠達說,“這就先留存查證。”接著把三份信件都交給了長聘,讓他收起,又朝段嶺說:“王山,放你一個省親假,十五日后,須得回府,為長聘先生打打下手,也好學著管點事。”
段嶺知道這下終于算是有驚無險地過了,朝牧曠達施禮,退了出去。
“我發現王山但凡發生何事。
”長聘說,“俱是這副模樣,倒是穩重。”
牧曠達答道:“堪當大任,來日可慢慢培養,沖著他與磬兒這情誼,倒是難得的,長聘,咱們的計劃,又得改一改了。”
長聘沉默片刻,而后點了點頭。
這一天里陽光燦爛,皇宮中,李衍秋坐在殿內,身邊只有一個鄭彥。
“你開什麼玩笑。”李衍秋聽完之后,眼睛瞇了起來。
鄭彥沒有說話,只是看著李衍秋。
“還有誰聽到這話了?”李衍秋問。
鄭彥答道:“昌流君、烏洛侯穆、武獨、馮鐸、以及相府的王山。”
李衍秋道:“絕不可能,山河劍法如何解釋?先帝會把劍法教給一個外人?”
“要是連先帝也被騙了呢?”鄭彥道,“畢竟阿木古并未說清楚是什麼狀況,若一開始就是烏洛侯穆先騙過了先帝……”
李衍秋道:“若是連他也被騙,我倒是無妨了。橫豎他認了,于我于你又有什麼關系?”
鄭彥:“……”
鄭彥實在沒想到,李衍秋居然會說出這麼一通話來。
“太子請見。”外頭唱道。
蔡閆來了,精神很好,看了眼鄭彥,點點頭。李衍秋注視蔡閆,蔡閆先請過安,跪坐在李衍秋身邊,不說話,只看著李衍秋笑。
“怎麼?”李衍秋說,“想朕了?”
“元人說是我假的。”蔡閆開口道。
鄭彥臉色微一變,李衍秋卻道:“不必管他們說什麼。”
蔡閆又說:“當年他們也這麼說。”
李衍秋端詳蔡閆,突然笑了起來,蔡閆卻不說話,眼眶紅了,轉頭望向一旁。
李衍秋伸出手,摟住蔡閆的脖頸,蔡閆便靠在李衍秋的肩上,嗚咽起來。
“你還惦記著叔說過的那些話,是不是?”李衍秋說,“你這人,和你爹一般的記仇,還記得你回來那天,也是這般抱著我哭。
”
蔡閆不住嗚咽,全身都在發抖,李衍秋說:“過了三月初三,就滿兩年了,叔都不哭了,你怎麼還跟個長不大的小孩似的。”
鄭彥卻仍在觀察蔡閆,眉頭深鎖,一時不知是真是假。
蔡閆在李衍秋肩前蹭,李衍秋便朝鄭彥示意,讓他退出去,抱著蔡閆,不住安慰他。
段嶺在紛揚的桃花中回了家里,武獨卻不知去了何處,段嶺一到家,先去找那兩封信,打開匣子,沒了!
段嶺驀然一驚,看見武獨在劍匣中留的字條:橋下等你。
段嶺險些被嚇得魂不附體,知道武獨只是逗自己玩,四處看看,疑神疑鬼的。收拾停當,出了家門,見巷里武獨身影一閃,想來雖然是逗他玩,卻也不敢離開太遠。
三山環江岸,九水繞春城,江州城中水道縱橫交錯,九座古橋置于青石板路上,小船來來往往,不少漁民撐著載滿河鮮的漁船,沿岸叫賣。桃花飛揚,正街距橋不遠,來到橋下時,段嶺到處張望,頭頂挨了一根桃枝,忙抬頭看。
武獨俯在橋欄前,朝下頭的段嶺笑,段嶺跑上橋去,武獨卻閃身走了。
“武獨!”段嶺道,“給我站住!”
武獨一本正經地在橋頭站著,段嶺走上前去,見陽光下,武獨的笑容英俊無比,一身黑色武袍在溫暖的春日里更是襯得身材英武,忍不住上前去,抱了下他。
“怎麼了?”武獨問。
“你怎麼了?”段嶺也問,“東西呢?”
武獨拍拍劍鞘,答道:“劍在人在,劍亡人亡。”
段嶺扶額,說:“怎麼都喜歡把重要東西藏在劍鞘刀鞘里。”
不過也是,除了阿木古這倒霉鬼,只要是隨身攜帶的東西,刀劍的鞘是最好的藏物處,畢竟對于刺客來說,幾乎是劍不離身。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