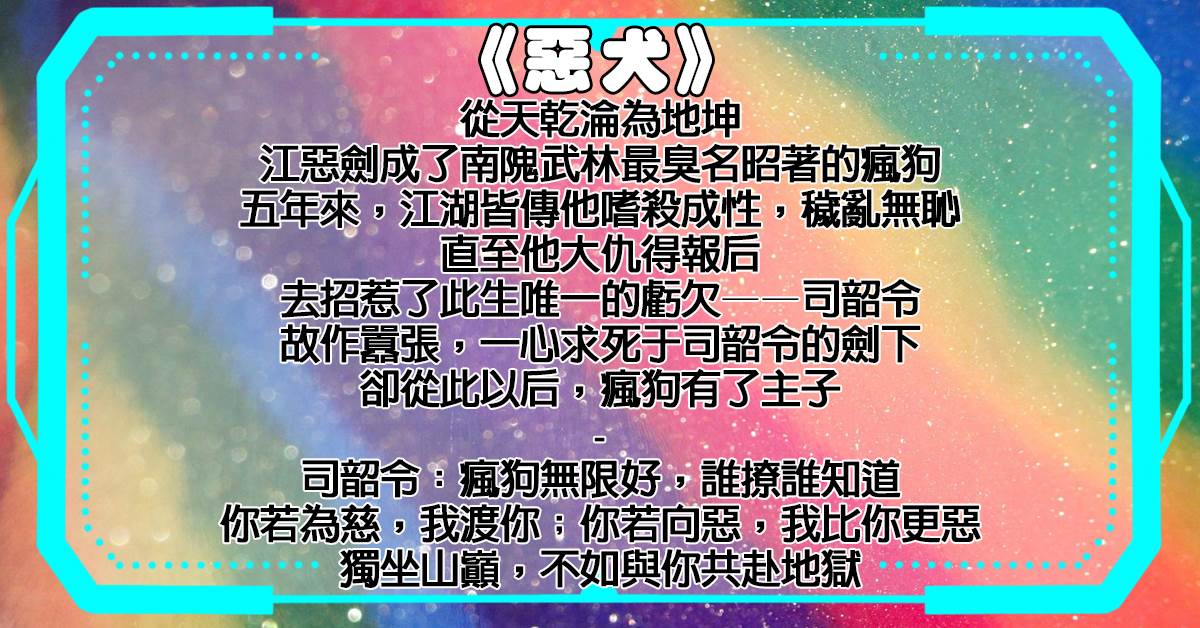《惡犬》第243章
包括與他距離最近的祁九坤,自他一動身,便注意到他的神色不對,隱約猜到什麼一般,并未多問地與他一同離開。
而敕風堂的內衛們絕非祁九坤的對手,無歸身為鬼門右使,內衛們更不可能傷及他,所以另一邊的司韶令,也便一直不曾仔細留意他們。
“那個祁大夫沒有回來?”
此時不世樓內,見司韶令面容有異,他面前的司瀾最先意識道。
“我倒還想問問你,他原來這般身手不凡,可是什麼隱退的江湖高手?”
司瀾再度詢問間,她一旁的扶心大師卻是若有所思,不過并沒有開口。
只聽司瀾又安慰司韶令道:“這里應沒幾個人是他的對手,說不定他只是臨時想到其他事情,等等便會回來,你不需過于擔憂。”
他們并不認得無歸,所以只以為司韶令是在擔心祁九坤的安危。
但若是祁九坤一人不見蹤影,尚可以認為他或許有自己的計劃,畢竟他獨來獨往慣了,此次出現在敕風堂,也實屬突然。
可是司韶令心里清楚,以無歸現今傷勢,不可能無緣無故便不見了。
他們二人很可能就在一起,遇到了什麼他不知道的問題。
而思忖間,方才魏珂雪那過于詭異的笑容不時侵入司韶令眼前,更令他心神不寧地忽然大步朝外走去。
“你們走吧,”屋外微涼的風卷起,司韶令迎著久違而灼目的日光,抬袖重新系緊遮擋住雙眼的黑紗,只留下這冷淡的幾句,“不必再勸我,我自有打算。有江惡劍在,也無人能傷我。”
的確,寸步不離跟在他身后的江惡劍,已然像個所向披靡的閻王,根本無人能靠近司韶令半步。
反倒是他們身為南隗幾派掌門,仍有對此行不明所以的眾多弟子們在等他們決策,加上針對魏珂雪的處置,也需盡快給與五派所有人一個交待,實在不便一直留在敕風堂內。
于是眼看著司韶令消失于幾人視野,僅有昭蘇不顧司瀾阻攔地又一次跟了上去。
“她沒有惡意。”
而昭蘇只能遠遠跟在他們二人的身后,腳下偶有過急時,察覺江惡劍一臉戒備地欲向后出手,司韶令沉聲止住他。
再怎麼說,若沒有昭蘇,江子溫或許早已被當初的天墟弟子發現,此后拜入天墟,抑或是由他人收留。
倒不一定會有何兇險,甚至可以說比這五年來與江惡劍相依為命要好過得多。
但是沒有了江子溫,他難以想象江惡劍又會是怎樣一副光景。
因而盡管仍感到昭蘇對自己存有少許不信任與敵意,司韶令看了一眼同樣停下的她,眸底冰雪微浮起一絲溫度。
“你過來。”他竟對昭蘇道。
“……”
昭蘇與他對視須臾,最后一步步走了過來。
他們眼下已然處于神門的拂云神宮附近。
“你去替我看看,青冥可有被帶進去。”司韶令也不與她客氣,徑直又道。
司恬爾向青冥套取消息,想必要先回到她這神門,司韶令暫時想不出具體聯系,只下意識覺得,無歸和祁九坤的失蹤,大抵與司恬爾有關。
若司恬爾安然無恙,他再另尋其他。
而他和江惡劍倒也能下去查探,卻勢必會驚動神門眾人,為避免不必要的爭端,不如讓輕功了得的昭蘇代勞,可省去很多時間。
“……”
昭蘇瞪了他片刻,像在判斷他是否意圖甩掉自己。
直到司韶令見她沒有動作,不欲耽擱地轉身自行走向拂云神宮,眼前驀地一閃,隨著輕如飛燕的虛影一瞬潛入宮內,本來站在他們身后的昭蘇已經依他所言地動了身。
心知越是這種時候,越該冷靜下來,司韶令緊蹙著眉頭等待間,稍微閉目,徹底隔絕頭頂燦陽。
卻不過片晌,還是沒來由地有星點濕跡沾濕了他的薄紗。
那是一陣連司韶令自己也說不出緣由,心間突如其來的悶痛。
他也不明白魏珂雪最后的一笑為何像一把剖骨刀,始終在他的骨肉間起落,似乎有什麼十分重要的東西,就那麼被一寸寸地剖離。
若不是突然有陰影當頭擋下,他險些就要倒在這熊熊火海般的烈日。
是一旁對他目不轉睛的江惡劍。
見司韶令原本挺直的身軀忽地微晃了晃,江惡劍忙一手扶住他,一手抬起,并攏幾指遮去了落在他眼睫上的日光。
可司韶令睜開眼,隔著一層薄紗,依舊能看到充斥在他眼底的一片赤紅。
“他們不在,”也就在此時,昭蘇果真動作快極,已最快的速度穿梭于整個拂云神宮,幾乎眨眼功夫便回到他們面前,并將她從宮內侍使口中聽來的消息告訴司韶令,“就在我們到這里的前一刻,他們去了青鄴王庭。”
“……”
司韶令一怔。
青鄴王庭?
司恬爾已帶回了青冥,又去那里做什麼?
沒有青鄴王的傳召,即便是他這敕風堂堂主也不可能輕易進去,她為何會突然跑了去?
青鄴王庭是青焉自幼住所,與她相熟之人應不少,豈不是容易暴露?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