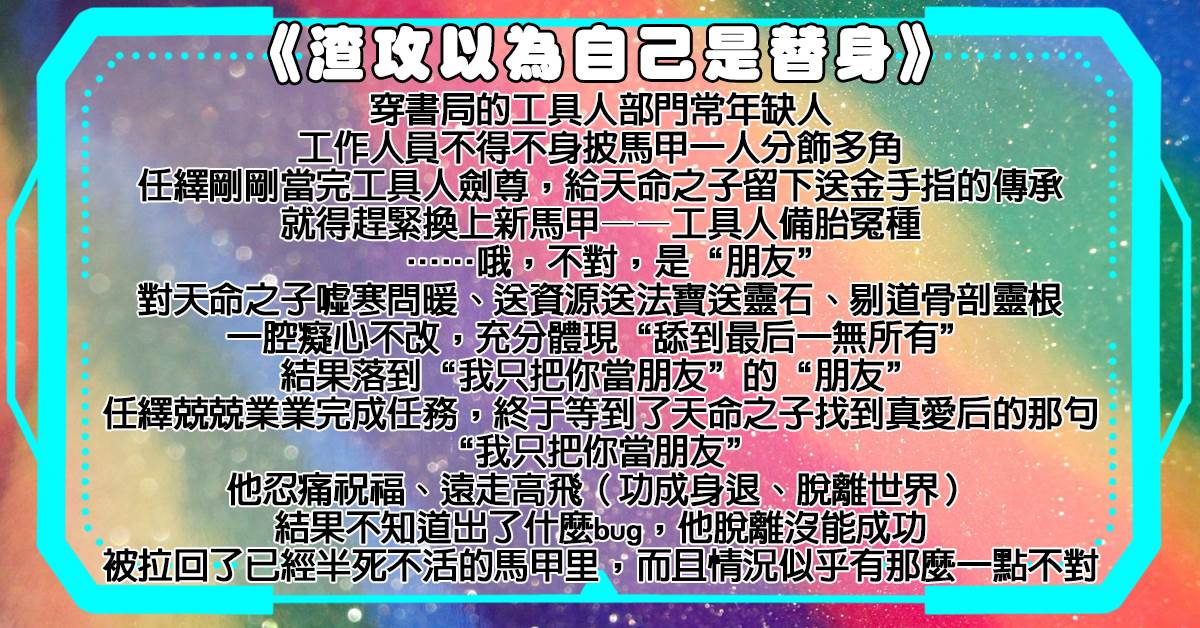《渣攻以為自己是替身》第95章
最開始說話的那仆役聲音又壓低了一成,像是說什麼隱秘一樣,小聲“什麼千年靈芝、萬年玉髓的, 我瞧著那人想要的可不僅僅是這些。”
另一個人似是愕然“這還不夠?!要是我得了但凡其中之一,恐怕做夢都要笑醒。”
蕭寒舟繃緊的唇角都在發顫,他在心底嘶聲反駁怎麼會夠?如何能夠?!!
對比阿繹為他做的,他的這些連千分之一、萬分之一都無!如何談一個“夠”字?!
蕭寒舟的心音自然無法傳入鏡中,倒是先出聲的那仆役似乎被另一個人的回應逗笑了,在“嗤”的一聲后, 笑斥“瞧你那點出息。”
另一個人也不惱,自嘲了幾句“眼界如此”之后,又連忙追問到底是怎麼回事。
先頭那個人四下瞄了瞄, 又比劃了個附耳過來的姿勢, 等身旁的人會意湊過來,他壓低了聲音,小聲“上個望日,我從家主書房外經過,正瞧見那人被家主趕出來,衣衫不整的、還露著一小截腰……那白的啊,汗珠凝在上面、真真似玉一般, 嘖嘖、也虧得家主忍得住。”
鏡外的蕭寒舟臉色已然鐵青。
因果鏡顯現出的畫面限制,蕭寒舟只能看見那邊隱隱綽綽的人影,并不能看見兩人的相貌, 又因為鏡內鏡外的隔絕,他連分辨神識都不能, 不過他仍是將兩人的聲音都死死記住了。
那仆從剛剛提起了“望日”, 有了這詳細的時日提醒, 蕭寒舟倒是想起了那一次到底是怎麼回事。
是阿繹在外時遇到了仇家,身中牽絲蠱。
他那日為解蠱毒而來,只不過阿繹最不喜人見自己狼狽的樣子,所以蠱毒剛解,便不顧身體尚虛弱、匆匆離去,應當就是那時候沒有防備,才不巧被那說話人撞見的。
而且阿繹的那仇家……
這次在因果鏡外以旁觀者的姿態重新看了那一遍過往,蕭寒舟才知曉,那仇家如何算是阿繹的仇家?那分明是他的仇家!是他當年在苗寨九族眼皮子底下取走了他們視為囊中之物的鳳凰引,阿繹為了幫他引開追兵,主動暴露,從此以后追殺不斷。
這本就是他惹得禍事,也本該是他的仇人。
阿繹只是在代他受過罷了。
……非但代他受了苦,還要被人如此指指點點。
一時之間,蕭寒舟竟分不清心底那些恨意多少是對著那些亂嚼舌根的人,又有多少是對著自己。
鏡中之人卻不知外面蕭寒舟的心情。
八卦熱鬧人人都愛,更別提這種艷情軼事。他們懼于蕭寒舟的威嚴不敢直接說家主如何,但是落到任繹身上就沒那麼多顧忌了,兩人嬉笑著說了不少葷話,直讓聽的蕭寒舟后槽牙都咬得嘎吱作響,等到終于調笑完了,又好似可惜一樣嘆“不過他那苦心謀劃注定要落了空了,誰不知道咱家主對白家的那位少爺情根深種,十多年過去了,還是念念不忘。”
蕭寒舟早先便已知道了他和白盡流謠言,本來只以為是些無根無據的流傳,但是這會兒聽到家仆談論的語氣才知,這事在蕭家竟已像是共識。
果然,另一個人也應,“說得可不是嘛。早先就有人說,家主何時會把人接來,這不就是了嗎?連客房都沒特意準備,還直接住進家主院子去了。”
“我可聽人說,當日是家主直接將人抱進去的嘞。
”
“……恐怕過上幾日,這府上好事就將近了。”
“……”
兩人你一言我一語,蕭寒舟未曾想,自己那時為防萬一隱瞞白盡流的傷情,竟會造成如此結果。況且他要是沒記錯的話,盡流在蕭府養傷后不久,阿繹就要從玉云鄉回來了……
思緒剛剛轉到這里,蕭寒舟整個人就是一僵。
這因果鏡中映的是他和阿繹兩個人的過去,這家仆二人的對話他從未聽過,那麼這番話實際落入了誰的耳中自不必說。
蕭寒舟臉上的表情霎時空白了下去,只有眼珠緩慢地轉動。
鏡中的畫面就那麼大,就算蕭寒舟再怎麼不愿意承認事實,他還是在鏡子的一角看見了那個熟悉的身影。
身形單薄瘦削的青年就定定的站在那里,好似從一開始就未動一步,幾乎和周圍的環境融為一體。因為鏡中的人和物皆都無法以神識掃過,蕭寒舟竟于那兩個沒什麼修為的仆役一樣,先前將之忽略過去了。
蕭寒舟不由想到自己那時對阿繹是否知曉這謠言的憂懼。
現在看,阿繹何止是知道?!他聽到的部分要比他最初料想的更過分千倍百倍不止!
嘴唇早不知何時被咬得鮮血淋漓,看著那被紅楓擁簇其中身影,蕭寒舟嗆咳了一聲,靈力傷了內腑,竟有血從唇角緩緩溢了出來。
任繹正頂著小號和鴻虛子對峙著呢,眼前的景象卻一陣扭曲的眩暈。
在看清周圍的環境之前,他已經先一步察覺不對,自己原本已經按在劍柄上蓄勢待發的手不知道什麼時候換了個姿勢,好像正往外遞著什麼東西。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