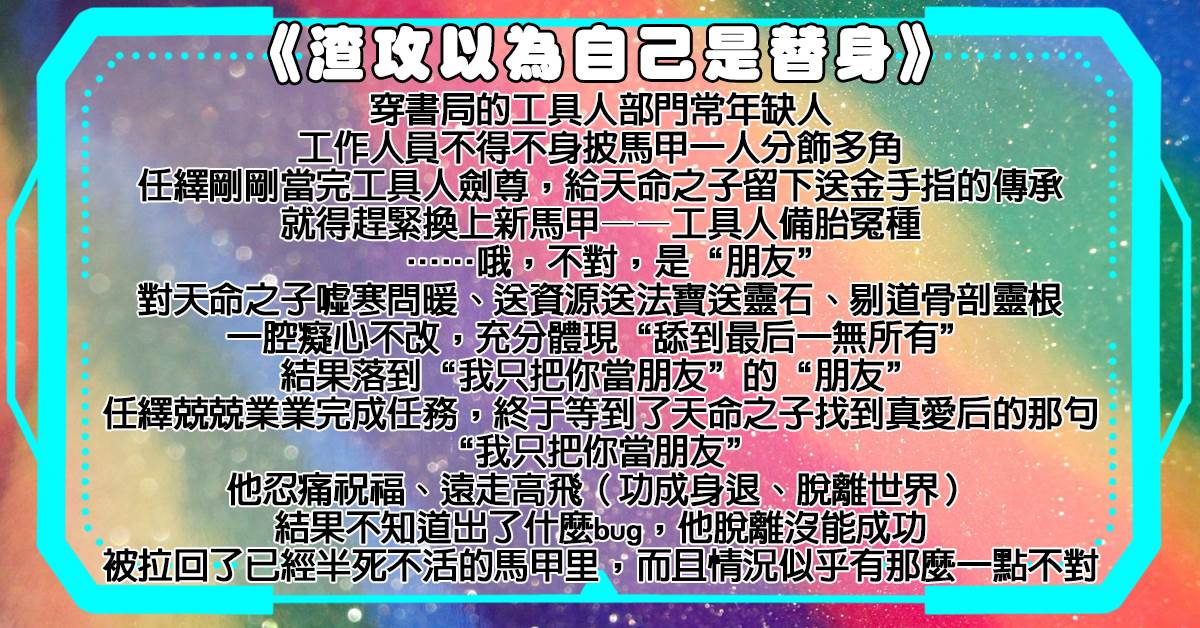《渣攻以為自己是替身》第18章
蕭寒舟接連問了好幾個問題,半點看不出平時寡言的模樣。
任繹還不及回答,就覺肩上搭了只手,將他往后帶了一步。
蕭寒舟原本焦急地詢問一滯,視線緩緩落在任繹的肩頭。
他手掌虛握了握,總算勉強止住下意識要動手的沖動。
阿繹不喜歡旁人碰他,這個人既然能讓阿繹這麼毫無防備,兩人必定是極熟識的。
只是這想法冒出來,蕭寒舟心頭那股不快愈甚。
來的自然是燕朔云,他倒不是因為接到師弟傳訊,只是恰巧路過。
那日關于“到底有沒有仇人”的話題,任繹都那麼說了,燕朔云也不好追問,只不過這幾日東洲來人,他還是特意推了離宗的任務、留在了宗門內以防萬一。
就比如說眼下這種“萬一”。
燕朔云笑答應了一句那接引弟子的“見過大師兄”,再看后者那滿臉“得救了”表情,更是忍不住搖頭失笑。
他倒也沒再叫人繼續為難,而是擺了擺手道“客人遠道而來,也該疲累了,你先帶人去安置吧。”意思就是這邊的事不用管,先帶著其他人走。
那弟子如蒙大赦,高聲應了句“是”,就火燒屁股似的跑走。
燕朔云看著那落荒而逃的架勢,忍不住在心底搖頭回頭得和素師叔說一聲,十六師弟這心態,還得再歷練歷練。
那些思緒只一閃而過,燕朔云很快就把注意力重新放回眼下的情況,只是這次表情可不像剛才那樣輕松。
他視線掠過蕭寒舟衣衫上的家紋,又不著痕跡的掃了眼任繹身上常常戴的那塊玉佩,這明顯同出一源的紋路讓人忍不住聯想是族人?兄弟?還是……別的什麼?
種種猜測在腦中成形,又被燕朔云一一揮散去畢竟人就在旁邊,他干嘛要猜呢?
想著,燕朔云搭載任繹肩膀上的手非但沒收、還又把人往自己這邊帶了帶,在對面陡然銳利起來的目光中,他笑問“阿繹,不同我引薦一下?”
就算燕朔云不提,作為同認識在場兩位的中間人,任繹也是要幫忙介紹的。
任繹開口,“蕭寒舟,蕭家的家主,是我在東洲的朋友。”
這個說法讓蕭寒舟不自覺的擰起了眉頭,那股剛剛消散下去的不適又升了上來,他們之間的關系不該輕描淡寫地以一句“朋友”概之。
像有什麼在胸腔堵塞,蕭寒舟下意識的想要出言反駁,但是臨到開口,又是一滯。
除了“朋友”,又有什麼呢?是“至交”?但又不僅僅如此。
任繹倒沒注意到蕭寒舟的思索,他先是回答了燕朔云的問題,又轉而介紹,“這位是燕朔云,燕兄,乃是玄清宗的大師兄。當年我剛到西洲的時候,多虧他救我一命,是我的救命恩人。”
蕭寒舟乍一聽聞任繹曾遭性命之危,當即臉色一變,也顧不得剛才種種思緒,立即想要追問,但是抬眼卻對上了燕朔云含笑看來的目光。原本到嘴邊的話霎時一頓,蕭寒舟皺起了眉。
但他還是先上下打量了一番任繹,見他氣色尚好、周身的靈力運轉也不像有什麼阻滯,這才放下心來,又轉而對燕朔云拱手,“既然是阿繹的恩人,就是我蕭家的恩人。日后燕兄但有吩咐,蕭家在所不辭。”
蕭寒舟這話說得極誠懇,但燕朔云卻眉頭一挑,在他動作的一瞬間,就側身避開了這禮節。
燕朔云聲音帶著點笑意,但是卻不太客氣的截斷了蕭寒舟的話,“蕭家主不必如此,我和小繹投緣,朋友之間、哪有什麼恩情不恩情的?倒是蕭家主,既是小繹的朋友,是我慢待了。”
燕朔云這一番話立刻將自己和任繹歸到了同一處,像是兩人是這邊的主人,蕭寒舟才是客。
這話委實讓人不適,蕭寒舟下意識的想要說點什麼反駁,但又想起了剛才那位玄清宗弟子對方追來時,看見任繹好似一點也不意外的樣子。
……阿繹入了玄清宗?
蕭寒舟忍不住生出這種猜測。
兩人之間已有足足三年未通音訊,蕭寒舟也不知任繹這些年到底發生了什麼,他想要仔細問,這邊又有個外人在場,不好細說。
他剛想要示意任繹之后再找個地方細談,抬眼卻看見任繹的目光正落在一旁的燕朔云身上。
蕭寒舟的臉色控制不住地難看下去。
久別重逢,本該是喜事,但卻不知為何,蕭寒舟只覺兩人之間從見面起便陰云籠罩。像是有什麼東西沉甸甸地壓在心頭,生生為這喜事包裹上一層塵霾。
而眼下這一幕,更是讓他控制不住的生出燥意來。
對蕭寒舟而言,像今日這種表露于外的情緒起伏極其少見,當年他面對屠門滅族的劊子手時且能夠不動聲色與之周旋,卻不料這次竟是這般狼狽。
他深吸了口氣,默默將靈力運轉了一個周天,頭腦冷靜下后、臉色也恢復平常。
“貴宗風水寶地、靈氣充盈,怎麼談得上慢待?只是我初到西洲,有許多不熟識之處……”他說到這里視線落在任繹身上,在任繹看過來時表情不自覺地放得柔和,“阿繹可愿意帶我認識一二?”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