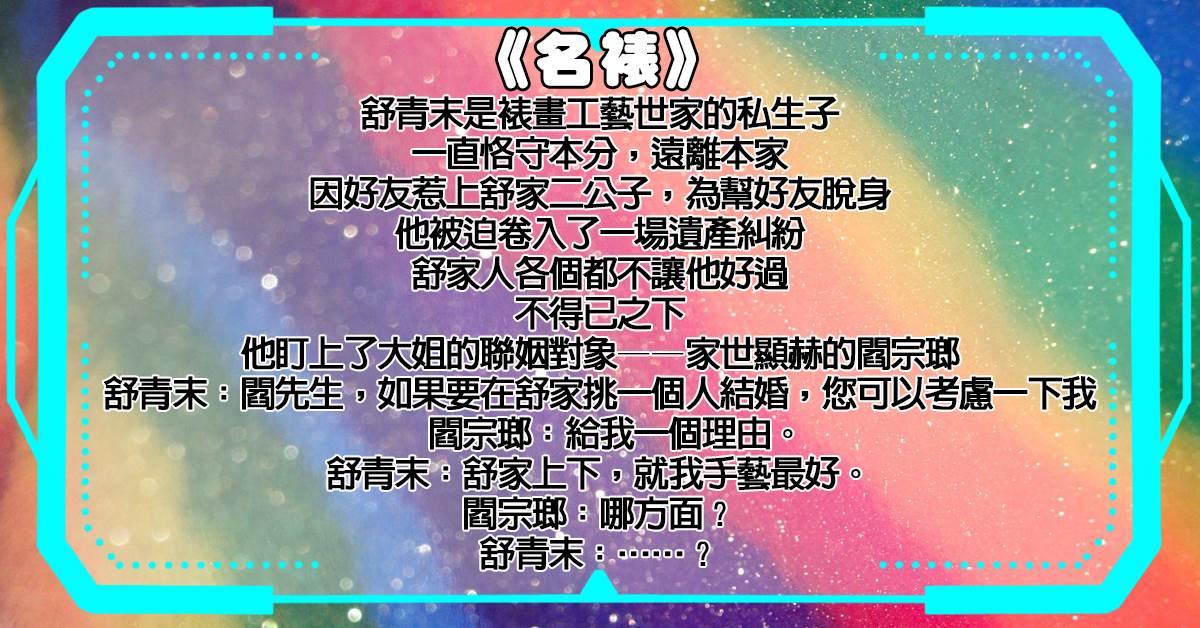《名裱》第74章
舒青末把他和方婉柔的交易說了說,當然也給駱梓杭分析了方婉柔的真實意圖。
駱梓杭聽完后把飲料杯一放,皺起眉頭道:“那你為什麼還要答應她?”
舒青末折著手中的餐巾紙,淡淡地說道:“因為我需要一個機會。”
無論是工作還是進學,舒青末都需要一個契機,才能克服時間上的硬傷。
就好比之前他偶然之下得到鄭功勛的賞識,被帶去新疆參與國家項目,接著又偶然之下結識常月娥,獲得去北京博物院工作的機會,這些都是契機,大大縮短了他正常前進的道路。
因此他若想短時間內搞垮方婉柔,就不能坐以待斃,等待契機自己出現,而應該抓住每一個機會,為自身創造有利條件。
綜藝節目就是擺在舒青末面前的一個機會。
盡管這個機會是一把危險的雙刃劍,若是沒有把握好,容易反噬到自己。
但如果舒青末把握好了,那他就能借此在圈子里站穩腳跟。
在說這些話時,舒青末的語速一直不緊不慢,臉上也沒有泄露出任何情緒,周身包圍著一種運籌帷幄的從容之感。
駱梓杭全程聽得一愣一愣的,手上拿著的烤串早已涼了也沒有發現。
半晌后,駱梓杭回過神來,放下烤串靠在椅背上,遠遠地打量著舒青末道:“老弟,你變了。”
舒青末挑了挑眉,拿起飲料道:“你穿一身西裝,好意思說我?”
駱梓杭摸了摸后腦勺,難為情地說道:“我這不是工作需要嘛。”
舒青末啜了一口飲料,無奈道:“我這是生活所迫。
”
“哎。”駱梓杭嘆了一口氣,又重新拿起烤串道,“你有沒有發現,我們都長大了。”
“是啊。”舒青末也有些感慨,“被迫長大。”
校園到社會的過渡最能改變一個人的性格,周遭環境發生劇烈改變,接觸的人和事也不再局限于校園之中。
如果說出生伊始到畢業之前是從零到一的過程,那麼適應社會就是短時間內從一到百的過程。
回過頭去看,舒青末還曾經擔心他和駱梓杭的關系會因告白而變得別扭。
但現在看來,他完全不需要擔心,因為駱梓杭不可能會一直喜歡他,除非兩人還待在校園之中,周圍的環境永遠不改變。
想到這里,舒青末放下杯子,用審問的語氣對駱梓杭道:“你老實交代,你是不是有新情況了?”
駱梓杭沒聽懂舒青末話里的意思,大喇喇地反問道:“什麼新情況?”
舒青末點到即止:“你的同事。”
駱梓杭擼串的動作一頓,差點沒嗆著。他喝了一口飲料,神色不自然道:“你怎麼知道?”
“我還不了解你嗎?”舒青末笑了笑,“你那同事對你說話態度那麼不好,就你這暴脾氣,還不偷偷給我吐槽兩句?”
“咳咳。”駱梓杭尷尬地清了清嗓子,“他確實比較特殊。”
舒青末好奇地問:“是誰?”
“杜老的孫子。”駱梓杭撇了撇嘴角,視線落在烤串上,“人家不可能看得上我。”
杜文笙的地位絲毫不比舒青末的爺爺差,況且他尚在人世,又在北京這寸土寸金的地界擁有私人博物館,可見他的孫子一定出身金貴,眼界也不會很低。
“所以你這是打算單戀到底了嗎?”舒青末好笑地問道,“不愧是你,駱慫包。
”
“喂。”駱梓杭不滿道,“你怎麼又提這個外號。”
小時候駱梓杭怕鬼,舒青末的母親去世后,他打死也不敢踏進舒青末的房子一步,因此光榮地獲得了這個稱號。
不過后來他越來越有男子漢氣概,舒青末也已經很久沒有這樣叫過他了。
“你難道不是嗎?”舒青末道,“我舉個不恰當的例子,你要是早幾年追我,說不定我們倆現在都領證了。”
“我看你這是站著說話不腰疼。”駱梓杭不爽道,“你知不知道喜歡上一個人會變得小心翼翼,那是說追就追的嗎?”
舒青末當然知道。
這些日子,他內心無比迫切地想要見到閻宗瑯,想依偎在他身邊跟他說話,聞他身上熟悉的香水味道。
但他不敢貿然買張機票飛來北京,因為他所有的理由只有一句“我想見你”。
他知道閻宗瑯不會喜歡這個理由,會覺得他還是小孩兒心性。
所以要說小心翼翼,他完全能夠感同身受。
只不過他和駱梓杭唯一不同的是,他敢于采取行動,抓住一切機會。
至少在幾個小時之前,他和閻宗瑯還相隔上千公里,而現在他來到了他所在的城市。
“算了,你這母胎單身,你懂什麼。”駱梓杭沒勁地說道,“反正追人這事兒沒你想象中那麼簡單。”
舒青末收回思緒,笑了笑道:“是你想復雜了。”
第二天一早,舒青末帶著四幅四大天王圖來到了北京cbd區域的一棟寫字樓下。
等了大約五分鐘后,陳秘書的身影出現在闊氣的自動感應門后。他三步并作兩步來到舒青末面前,詫異地問道:“舒少爺,你怎麼來了?”
“陳秘書,你就叫我小舒吧。
”舒青末說著把手中的畫遞了過去,“麻煩你幫我把這四幅畫轉交給閻先生。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