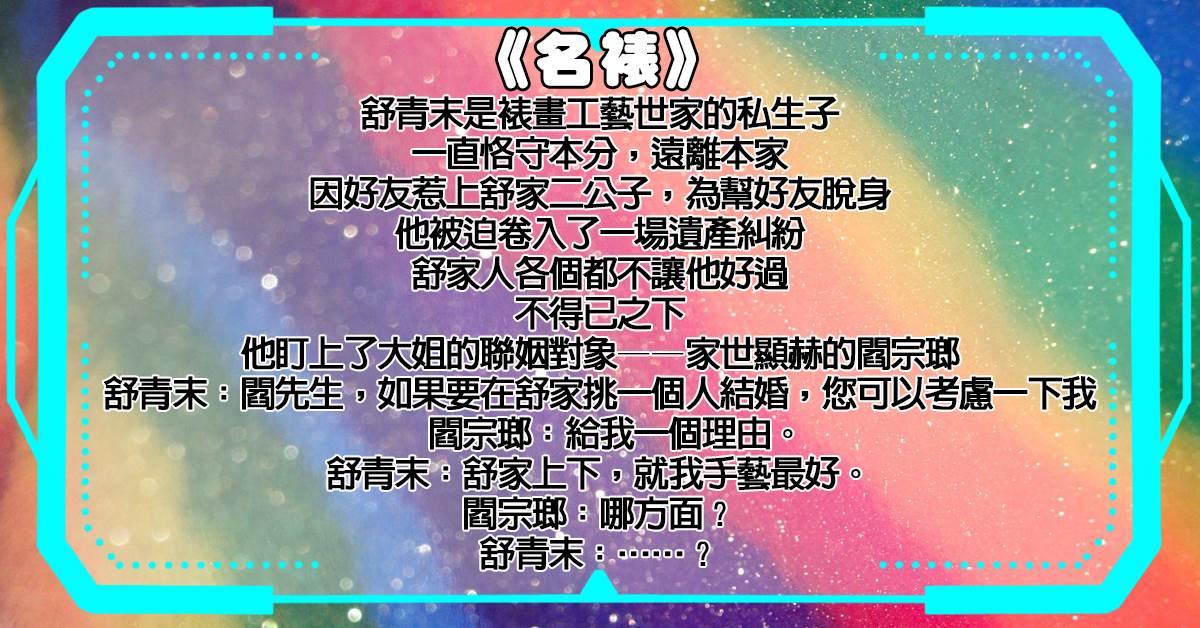《名裱》第42章
每到周末,度假村便會人滿為患。大多都是附近市區的人,來石獅山玩個兩天一夜。
周六夜里工作人員會在度假村的門口組織篝火表演,許多客人都會來湊個熱鬧。
不過舒青末和閻宗瑯并沒有參加,他們住宿的小木屋位于度假村最里面,也是整片區域海拔最高、視野最開闊的地方。
他們只用坐在小木屋門口,便能一邊享受安靜的環境,一邊俯瞰下方熱鬧的場景。
在小木屋旁用過晚餐之后,服務人員撤走了餐桌和燒烤架等一系列物品,陳秘書也帶著司機和保鏢回到了各自的小木屋里休息,小小的篝火旁邊很快就只剩下閻宗瑯和舒青末兩人。
下方的大型篝火旁有歌手在表演,四周圍了一圈又一圈的人。
原本舒青末和閻宗瑯都在靜靜地聽歌手唱歌,結果舒青末一個噴嚏打破了這安謐的氛圍。
山里早晚溫差大,剛才吃著燒烤時舒青末還沒注意,現在吃飽喝足后,他便隱隱覺得有些發冷。
“冷嗎?”閻宗瑯從下方收起視線,看向舒青末問。
“還好。”舒青末用食指擦了擦鼻尖,肩膀縮得更緊,任誰看也不像是還好的樣子。
“要不進去?”閻宗瑯提議道。
“沒關系,再看會兒吧。”舒青末看了眼時間,現在才八點多,就算回到小木屋中他也無事可做。
“那等我一下。”
閻宗瑯說完之后起身回了一趟他的小木屋,等再出來時,他的手上赫然多了一件西裝外套。
他把西裝外套抖開,搭在了舒青末身上,一股熟悉的香水味撲面而來,舒青末難為情地收了收下巴,小聲道:“謝謝。
”
蓋上外套之后,舒青末的身上暖和了不少,但他的右手仍舊有些不適。
這些年來,舒青末的右手堪比晴雨表,如果頭天手掌隱隱作痛,那第二天必定降溫。特別是到了冬天,舒青末幾乎暖手袋不離手。
為了緩解不適,他在西裝外套下用左手按摩右手,西裝外套也隨之一下一下地拱起,同時還發出細微的沙沙聲。
閻宗瑯很快注意到了舒青末怪異的舉動,他看著西裝問:“手不舒服?”
那個位置只能是手在運動,舒青末沒法含糊過去,只好道:“嗯……天氣冷了會有點疼。”
閻宗瑯朝舒青末攤開手掌,道:“手給我。”
舒青末不太喜歡把右手完整地暴露在別人面前,他沒有動,婉拒道:“不用。”
閻宗瑯皺了皺眉,不容拒絕地沉聲道:“不要讓我說第二遍。”
舒青末磨磨蹭蹭地伸出右手,放在了閻宗瑯的掌心之中。
閻宗瑯的手掌很大,手指比舒青末的手指長出了一個指節,骨節分明卻并不干瘦。他包裹住舒青末的右手輕輕按了按,問道:“這樣疼嗎?”
舒青末搖了搖頭,他只感到手背上傳來的溫暖順著皮膚到達了指尖,讓他整個人都不再感到寒冷。
閻宗瑯就這麼用自己溫熱的大手包裹住著舒青末的手,兩人繼續看下方的表演。
腳邊半米多高的篝火發出噼里啪啦的響聲,示意著柴火的充分燃燒。明明火勢和剛才并無變化,但舒青末卻總覺得瑩瑩的火光烤得他渾身發熱。
他抽了抽手,對閻宗瑯道:“閻先生,我不冷了。”
閻宗瑯并沒有松開,他轉過頭看著舒青末問:“你會看手相嗎?”
“手相?”舒青末搖了搖頭。他多少知道手掌中圓弧的那條線代表生命線,但其他的一概不知。
閻宗瑯用拇指輕輕撥開舒青末蜷著的四指,在火光的照耀下,一條蜈蚣躍然出現在舒青末的手掌當中。
舒青末下意識地握了握拳,不想把那丑陋的手術疤痕展現在閻宗瑯面前。
“能給我看看嗎?”閻宗瑯停下動作問。
這句話的語氣很隨意,舒青末相信只要他不同意,閻宗瑯也不會強求。但最后他只是抿了抿嘴唇,還是緩緩松開了手指。
“你的手型很好。”閻宗瑯將舒青末的四指合攏,“沒有閉不攏的指縫,你知道這代表什麼嗎?”
舒青末當然不知道,他按著商人的思維猜測道:“適合數錢嗎?”
閻宗瑯笑道:“不是,代表你能守住財,財運不會從你的指縫中溜出去。”
舒青末這時候總算對“手相”一詞有了點實感,說到底不過是封建迷信。
他沒有忍住,勾起嘴角偷笑了一下,閻宗瑯立馬注意到了他的表情,挑眉問:“笑什麼?”
“沒有。”舒青末搖了搖頭,“我只是覺得……好像做生意的人都很迷信。”
舒青末是絕對不迷信的,他不相信鬼神的存在,如果他信,那他也不可能在母親去世后的屋子里獨自生活。
不過話說回來,他倒沒有嘲諷閻宗瑯的意思,他只是發現閻宗瑯也有這樣一面,覺得很有趣。
“商人的迷信也分種類。”閻宗瑯沒有介意舒青末的話,語氣平淡無波地說道,“像我,我就只撿聽好的聽,壞的一概不聽。”
舒青末見閻宗瑯沒生氣,膽子大了一些,說道:“這是自我麻痹吧。
”
“這叫心理安慰。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