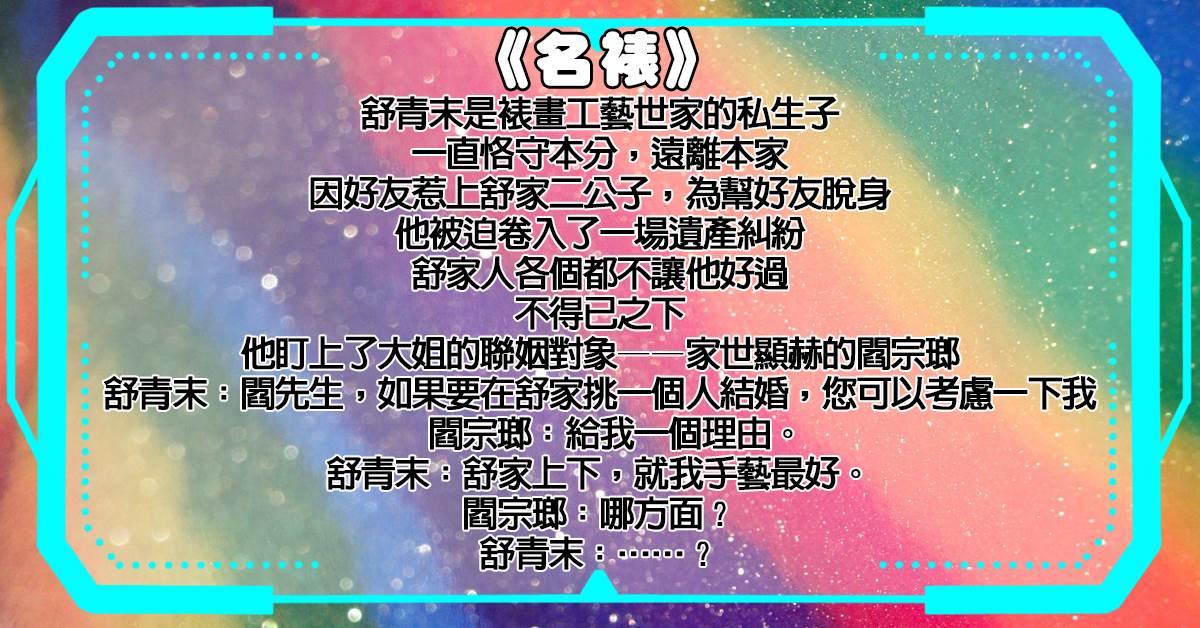《名裱》第2章
舒青末的右手曾經受過傷,直到現在中指和掌心的骨頭上還打著鋼釘,無法做精細的活。
原本他小時候在國畫上極有天賦,也正因如此,曾短暫地獲得過舒國華的歡心。
然而在受傷之后,他的右手拿不穩毛筆,不得不放棄國畫,改畫油畫,因為油畫只需要拇指和食指就能握住筆桿。
現在的舒青末是華南美院油畫專業的大學生,不過背地里,他一直在用左手練習工筆畫(注),水平早已超過了當年。
右手畫油畫,左手畫國畫,這是舒青末的特長,也是他的秘密。
所以準確來說,此時此刻在窗邊的畫案前,舒青末用左手拿起了毛筆。
宣紙上很快出現了幾根墨色鐵線,傳神地勾勒出姿態夸張的黃袍道士。
舒青末熟練地運用手中的狼毫細筆,用點畫的手法突出黃袍上的重點,接著再細畫出道士手中的招魂鈴。
而就在舒青末畫得正起勁時,他左手邊斜對面的窗戶忽地被人推開,一個手拿香煙和打火機,滿臉煩躁的男人出現在了他眼前。
裱房的位置位于整棟建筑的角落,如果把這部分角落看作大寫字母“l”,那豎線的地方是長長的走廊,而橫線的地方就是裱房所在。
舒青末能看清斜對面男人的一舉一動,反過來說,那個男人也能看清他正在畫畫。
舒青末幾乎是條件反射地放下了手中的毛筆,有意思的是,對方也條件反射般地收起了不耐煩的神情和手中的香煙。
除去那西裝筆挺的身姿和朗目星眉的面龐,舒青末對這人的第一印象是他一定很善于偽裝。
只不過是眨眼的功夫,身上的氣質便判若兩人。
“你好。”閻宗瑯率先開口,對舒青末微微頷首。他的語調從容沉穩,眼神掃過窗框后的畫案,接著又回到了舒青末的臉上。
“你好。”舒青末禮貌地點了點頭,不動聲色地把手邊的毛筆推遠了一些。
按照當地的葬禮習俗,親屬佩戴黑色袖章,客人佩戴白色袖章。
舒青末看到對方胳膊上戴著和他同樣的黑布,懷疑這人是舒家的遠房親戚。因為若是熟悉這座宅子的人,應當不會來這個角落抽煙。
他好心提醒道:“你回到剛才上樓的地方,右轉走到底有一個露天陽臺,可以去那里透風。”
閻宗瑯順著舒青末的話回頭看了看來時的方向,接著對舒青末道了聲“謝謝”,關上走廊的窗戶轉身離去。
樓下放起了鞭炮,噼里啪啦的響聲震得舒青末耳膜都在發麻。
院落里彌漫起青煙,濃濃的火藥味飄到二樓,無論是聽覺、視覺還是嗅覺,都讓舒青末極度不適。
他本想關上裱房的窗戶,但又不想被樓下的人看見,最后只得用右手掩住了口鼻。
他重新拿起毛筆,在道士的腦袋上畫了一副耳機,又在他臉上畫了一個口罩,無聊地心想為什麼他不是神筆馬良,畫什麼都能變成實物。
好半晌后,鞭炮聲終于停止。
青煙散到空中,視野開闊起來,舒青末憋了許久,總算可以放開呼吸,但就在這時,他突然嗅到了一絲不屬于裱房的氣味。
那是一種淡淡的木質香氣,像是清冷的檀木香,卻沒有那麼純粹,似乎夾雜著低調的皮革氣息。
舒青末猛然反應過來這是香水味,他嗖地轉過腦袋,接著便看到了本該去露天陽臺透風的閻宗瑯。
“你怎麼在這里?”舒青末忙不迭地放下手中的畫筆,眼神不善地質問身后的人。
裱房不是私人空間,誰都可以進來。但這樣悄聲無息地走到別人身后,舒青末多少還是覺得有被冒犯。
“我有敲門。”閻宗瑯的語調依然很沉穩,不緊不慢地解釋道,“但你好像沒聽見。”
行吧,下面的鞭炮聲那麼大,舒青末聽得見才有鬼。
“你是舒家的人?”閻宗瑯掃了眼畫紙上那滑稽的道士,嘴角浮起一抹淺笑,看著舒青末問。
“不是。”舒青末下意識地做出了否定回答。他知道這人看到了他用左手畫畫,雖然他不怕暴露這一點,但也不想多生是非。
不再給對方繼續問詢的機會,舒青末直接轉身離開了裱房。
儀式結束之后,方婉柔差使傭人把舒青末叫到了負一樓的書房。
這個書房是舒國華生前工作的地方,使用的桌椅和書柜都由金絲楠木雕刻而成,價格極其昂貴。
整面墻的排柜里塞滿了古書和字畫,置物架上還擺放著不少古玩器件,光是這一間房,就不難看出舒家的家底有多殷實。
“這位是李律師。”
方婉柔介紹了一下坐在她身邊的中年男人,明明在場的人除了舒青末以外,還有她的大女兒舒夢芙和二兒子舒亦晨,但她的視線始終固定在舒青末身上,顯然這里不認識李律師的只有舒青末一人。
“接下來由李律師宣讀一下遺囑。
”
舒青末沒想到遺囑中第一個提到的人竟然是他。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