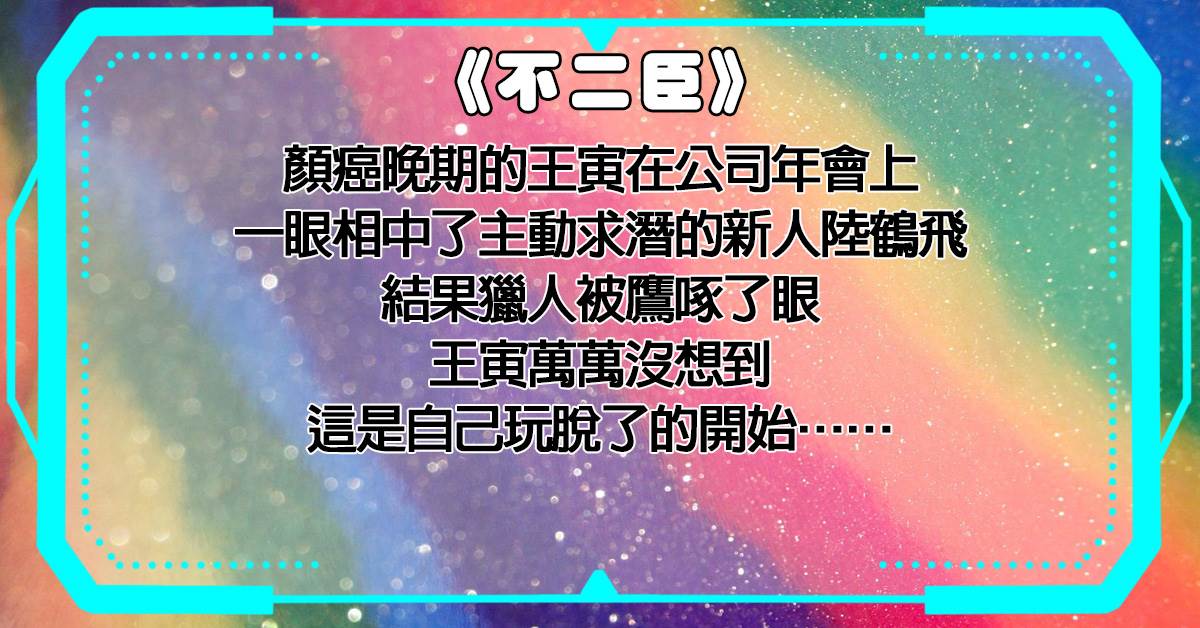《不二臣》第211章
等把他所能想到的最后一小節寫完之后,才說:“很想寫情歌,不會寫。”
花枕流問:“為什麼要寫情歌?”
“我有一個聽眾。”寧姜說,“從我出道,她就在聽我的歌,給我寫過很多信,在我最困難的時候,鼓勵我。好多年了啊,她為了做了許多,現在她要結婚了,我想送她禮物。可是我什麼都不會,只會寫歌。”
“那她一定是全天下最幸福的粉絲。”花枕流笑著說,“能夠在結婚的時候收到偶像的禮物。”
寧姜說:“我不是什麼,偶像。我……不是什麼積極的人,不能給別人,起到榜樣作用。我想和大家,做朋友,很平等的關系,分享我的音樂,和我想表達的東西,就可以了。”
“可能也就只有你一個人這麼想了。”花枕流聽寧姜破天荒的要給別人寫情歌,心里就泛起了酸。寧姜是個非常冷情的人,感知能力也弱,他的創作欲望在于表達,表達他用語言無法描述的內心世界。而在他的僅有的情感之中,是沒有一丁點留給愛情的。他從未寫過情歌,如一個苦行僧一般。
他沒有那樣的能力,以至于當他想人為的去做一些嘗試的時候,才發覺一切是都是那麼的難。
花枕流是不敢在寧姜面前提什麼情情愛愛的,他仿佛做了什麼虧心事的賊,無法光明正大的在失主面前聊起贓物。于是乎只能顧左右而言他地說:“我不在的這些時間里,我爸有找過你麻煩麼?”
寧姜回憶片刻,回答:“沒有,他,是個說到做到,的人。”
當年那一出著實是個鬧劇,花父提出了一個近乎不可能的要求,他想當然得認為沒有人是肯犧牲自己的一生去搭救一個曾經傷害過自己的人的,但是對方是寧姜,那麼一切就都不成立。
花父很氣憤,因為被人駁了面子,但是再怎樣惱羞成怒也不能把說出去的話再收回來。于是他徹底的選擇了眼不見為凈,與花枕流脫離了關系,從此生生死死不再想干。這樣一來,自然也不會管寧姜怎麼活著。
花枕流在美國的這一年多的時間里,寧姜的生活其實很簡單,要麼在家里呆著,要麼去工作室里,他住在花枕流這里,偶爾回自己的住處,他不清楚花枕流什麼時候回來,心中也了無牽掛。
“他也就只有這一個優點了。”花枕流嘲笑道。他還握著寧姜的手,很難焐熱,不由得叫他抓的更緊了一些。只聽腳邊一陣聲響,不知何時一直黃白相間的野貓蹲在面前,它不怕人,似乎認識寧姜,朝著他喵喵叫。
“你餓了啦?”寧姜問貓,“我今天,沒有帶吃的。你的同伴呢?”
貓像是回答一樣的又叫了幾聲,開始圍著寧姜的腳邊來回轉圈。
花枕流問:“你喂過它?”
“嗯。”寧姜點頭,“他們是去年夏天,生的一窩小貓。本來有六七只,院子里的人,很喜歡他們。但是野貓難過冬,去年冬天過去,就剩下了三只,它是其中之一。今年過去,不知道還能剩下,多少了。”他說完,輕輕的嘆了口氣,似乎為眼前這只貓的生計感到憂愁。
花枕流又問:“那它對你好麼?”
寧姜說:“給我叼過,死老鼠。”
花枕流笑了出來,說:“它喜歡你。”
“是麼?”寧姜問,“那我,可以養它麼?”
“為什麼不可以呢?”
“這里是,你家。”
花枕流一滯,柔聲說道:“這里也是你的家,你想做什麼都可以。就算不想當成家也沒關系……你有自由的權利。
”
“好。”寧姜簡單一字的回答。他的手抄進口袋里摸了摸,里面確實什麼都沒有,還翻出來給貓看了看。而后他起身往樓前走,還朝著那只貓招了招手。貓像是能聽懂他的話一樣,竟然真的跟了過去。寧姜蹲下來伸出手,貓就在他的指尖聞了聞,寧姜的手指去撓它的下巴,它的喉嚨里就發出了“呼呼”的聲響,好像很舒服的樣子。寧姜揉了它一會兒,站起了去了電梯里,對那只貓說:“你要來我家麼?”
貓猶豫了一下,還是慢慢的朝著寧姜走。
寧姜又抬頭看遠處的花枕流,問道:“你不回來麼?”
“啊……”花枕流應了一聲,趕緊快跑兩步進了電梯。電梯門關上的時候,花枕流站在寧姜一旁,小心翼翼的去摸寧姜的手,寧姜沒有拒絕,乖乖的叫他拉。
他一手牽著寧姜,一手抱著貓進了家門。寧姜在外面總是喂貓,但是沒有什麼養貓的經歷,花枕流更是連自己都養不好的主兒。二人先是給貓洗了個澡,隨后才看著網上的帖子檢查了一番,小區環境封閉,這貓又從來沒出去過,身上沒什麼蟲子,耳朵也干凈,洗澡時雖然很害怕的喵喵叫,但是不伸爪子也不咬人,洗干凈了把毛吹蓬松了,跟家養的也沒有什麼區別。只是它突然換了環境很膽小,一下子就跑去了床底下躲著。
“上面說,要帶它去醫院。”寧姜拿著手機一字一句地說,“做檢查。”
花枕流也是想起一出是一出,說道:“那我們現在去?醫院應該都開門了吧,我們去順道吃個早飯。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