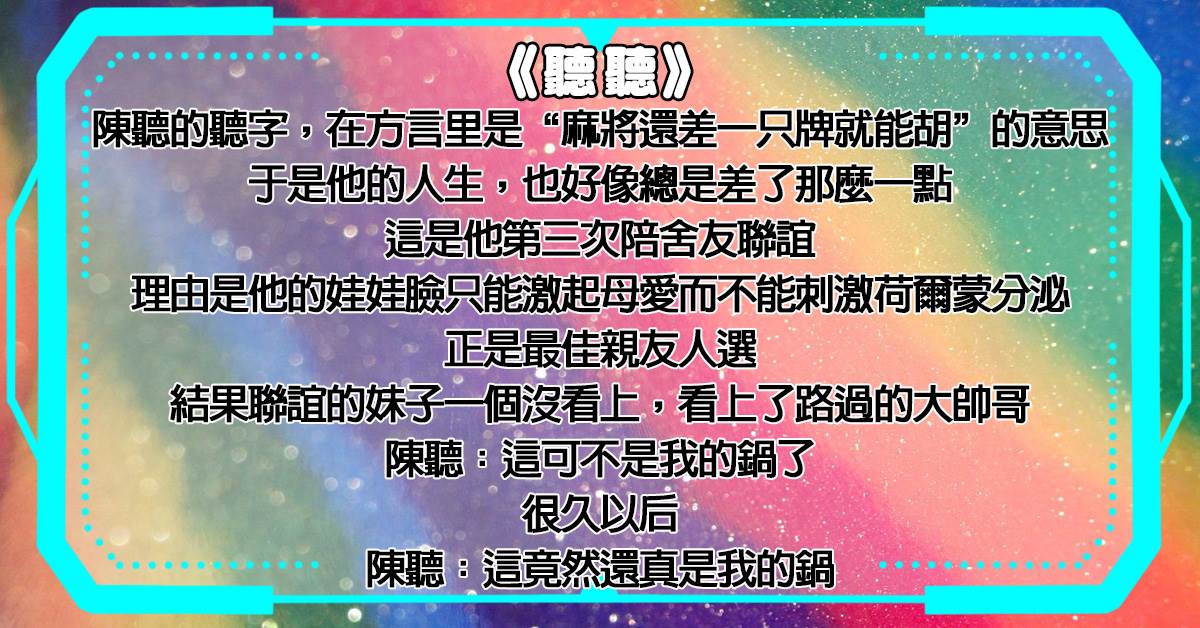《聽聽》第91章
陳聽:“你要給我捂痱子嗎?”
裴以堯:“擦汗。”
陳聽不明所以:“那你擦啊。”
裴以堯依言給他擦汗,柔軟的毛巾擦過他的鎖骨,再往上便是陳聽因為喝水而鼓動的喉結。他的目光盯著他,手雖然放了下來,但兩人間生人勿近的氣氛卻越來越濃。
這畫風,可不就不一樣了嗎。
跟這種gay里gay氣的粉色畫風相比,其他正在健身的男同胞女同胞們,覺得自己就像哼哧哼哧蕩秋千的山地大猩猩。
不知道為什麼,陳聽和裴以堯一來,大家都不好意思脫衣服了。
誰脫誰是gay。
好在大家的苦惱并沒有持續多久,陳聽也覺出了點尷尬,于是又放棄了健身房項目。雖然出柜成功,但他跟裴以堯并沒有特意在學校里公開,因為除了最為親近的楊樹林和卷哥等人,他們并不在乎其他人的想法,那也就沒有必要特別說明。
他倆既不遮遮掩掩,也不高調宣告,大家看到眼里是什麼那就是什麼。學校里當然不是所有人都能支持、理解他們,但比起更無情殘酷的社會,這里更包容、更多元化。
更不用說陳聽還有個隨時準備用八國語言跟傻逼battle的楊樹林,但很可惜,至今也沒人過來找茬。
楊樹林英雄無用武之地,陳聽便喊他一起打籃球。裴以堯不是愛吃醋麼,那他就不去健身房了,讓裴以堯手把手教他打籃球,總不醋了吧?
裴以堯確實不醋了,但因為楊樹林在,他又叫上了高鐸。
高鐸在上學期已經研究生畢業了,現在在博物館工作,每天朝九晚五,活得像個退休老干部。
但他每次過來打籃球的時候,還是一身阿瑪尼,手腕上戴著卡地亞,頭發也精心打理過,騷包得像是剛從巴黎回來。
楊樹林對此很是崇拜,還曾經問過高鐸為啥不干脆轉行做模特。高鐸回答說:“我是一個有追求、有崇高理想的人。”
楊樹林很感動,然后就被高鐸在籃球場上用籃球打爆了。
狗哥也已經畢業了,據楊樹林說他進了一家出版公司,正在社會這所大學里苦逼的熬資歷。但楊樹林還是沒能坐上記者團團長的位置,因為他到現在也還是交不出一篇讓人滿意的稿子。
他的文筆就像他的籃球技術一樣,永遠漏洞百出。
陳聽的籃球技術也不行,但沒關系,他就是來減肥的,隨時隨地可以祭出他的秘技——拍皮球。
N大的籃球場大多沒有空著的時候,裴以堯有時會跟其他來打籃球的人組隊打比賽。陳聽便在旁一邊拍皮球一邊看,他喜歡看裴以堯打籃球,更喜歡看他贏。
楊樹林便打趣說:“聽聽你還記不記得五塊錢那件事兒?”
“記得啊。”陳聽哪能忘記呢,這事兒到現在還掛在論壇上,時常被人拿出來溫故知新。學長學姐們借此教育新來的學弟學妹,看到沒,不要妄想泡校草了,沒用的。
思及此,陳聽又站起來:“去不去買冰棍啊?”
“現在去啊?裴以堯還打著呢,待會兒他看不見你又該找了。”
“管他呢,我們走。”
陳聽撒丫子就跑,速度還是一如既往的快。
楊樹林趕緊跟上,兩人跑了好遠終于跑到了小賣部,各自一根老冰棍一瓶水,坐在小賣部門前的臺階上吃得歡。
不一會兒,一道陰影罩住了陳聽。
陳聽抬頭看,只見裴以堯微喘著氣站在他面前,被汗水沾濕了的頭發往后撩著,眉梢鋒利,又酷又帥。
“已經打完了?”陳聽詫異。
“打了半場。”裴以堯答。
“那你怎麼過來了?”
“我打給你看的。”
言下之意就是,你人都走了,我打了也白打。陳聽秒懂,拍拍身旁的空位,又把水遞過去:“坐會兒啊。”
裴以堯坐下,擰開蓋子仰頭咕嘟咕嘟灌了幾大口,手肘撐在膝蓋上,每一塊肌肉的線條都自然流暢。
陳聽耳朵有點紅。
楊樹林默默坐遠了一點。
裴以堯把水放到一邊,轉頭看著陳聽手里吃剩一半的冰棍,問:“好吃嗎?”
陳聽點頭:“好吃啊,這個有點像我們小時候吃的那種棒冰的味道。我上次不是在家里做了嗎,就跟那個差不多。”
聞言,裴以堯直接低頭就著他的手咬了一口,用事實說話:“嗯,確實差不多。”
“誰叫你吃了!”陳聽要炸毛,冰棍本來就剩一半了,他還吃了那麼大一口。他現在在減肥呢,一天一根冰棍不能再多吃了。
“我再給你買一根。”裴以堯很淡定。
“不稀罕。”
“慕斯蛋糕?”
陳聽氣死了:“我警告你不要再跟我提蛋糕不然就跟你分手。”
裴以堯果然換了一種說法:“我媽喊你周末回家吃飯。”
陳聽皺起小眉頭:“那不叫吃飯,那叫喂豬。”
“牛肉面也想你了。”
“呵。”
我看你滿腦子黃色廢料。
陳聽非常想拒絕,但長輩提出了邀請,他當然不能真的拒絕。于是周六一到,他又坐上了裴以堯的車,踏上了口斤口斤之旅。
其實他的身上還是不怎麼胖的,雖然不瘦,但看著很勻稱。
只有那張臉永遠嬰兒肥,一胖就會有雙下巴。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