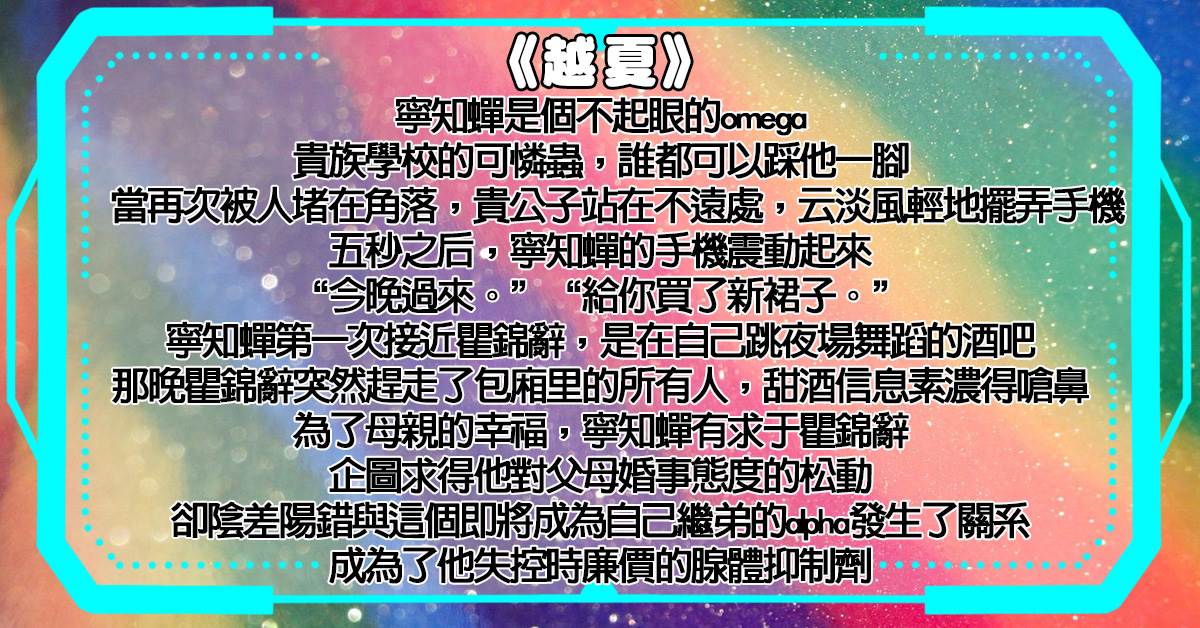《越夏》第9章
宋易勛要帶寧知蟬去看的那間藝術館建在海港附近,入夜之后,周圍的碼頭港灣亮起燈,錯落的暖白色建筑像一枚沉進海里的珍珠。
夜風有些冷,空氣潮濕,寧知蟬下了車,很輕地縮了縮身體。
照常來說,這個時間應該已經閉館,不過因為宋易勛是藝術館的投資人,他說想要來,館長便特意將閉館時間延后,并且在大廳相迎,親自從旁講解。
展館內陳列著許多藝術品,據說來歷珍異,而且價值不菲。
寧知蟬不像那些高門大戶家的矜貴公子,從小開始接受高等的教育,接受良好的藝術熏陶,館長口中名字很長的藝術家、陌生的藝術流派,他一個都沒聽說過,只能安靜地跟在后面走。
事實上,如果不是寧紹琴,寧知蟬想,自己是不會答應來和宋易勛一起看藝術展的。
他現在覺得有點冷,饑餓感后知后覺地涌現出來,寧知蟬突然想吃搬來南港之前、學校門口不太衛生的小館里賣十元一碗的雞湯小餛飩。
“知蟬。”
寧知蟬抬了抬頭,發現館長不知道什麼時候已經離開了,宋易勛站得有些遠,回頭看寧知蟬,向寧知蟬招了招手,寧知蟬只好走過去。
“叔叔不了解你的喜好,帶你來看這些,是不是覺得無聊?”宋易勛問道。
寧知蟬強顏歡笑地搖了搖頭,說不是,宋易勛便笑了笑,又問寧知蟬:“叔叔在這里存了一副私藏品,要不要一起去看看?”
寧知蟬沒有選擇地點頭說“好”,宋易勛很快帶著他走到展廳轉角處,穿過連接兩間展室的白色長廊,來到一扇不算太起眼的門前。
不遠處的展館負責人員快步走過來,恭敬地向宋易勛頷首,得到宋易勛授意之后,為他打開了面前的這扇門。
門內是一個不算太大的房間,沒有窗子,墻壁上貼著墨綠色的絨毯,壁燈發出的乳白色光線十分淺淡,顯得整個房間很暗,甚至有些輕微的壓抑。
寧知蟬站在門口猶豫著,一點也不想進去,但宋易勛語氣溫和地叫了他一聲,寧知蟬只好跟了上去,身后的門又被關了起來。
“知蟬,過來看。”
墻壁上掛著一副油畫,用深色的木框裱著,宋易勛站在畫前,看著畫框里的女人側影,在昏暗的光線中,看起來似乎比往常要顯得蒼老一點。
不知道出于什麼原因,寧知蟬突然想起在體育館的那天,散漫地倚在墻壁上,把獎杯送給漂亮女孩的瞿錦辭。
或許是因為寧知蟬偶爾發覺,他們父子之間有些微妙的相像。
他們眼睛里有時會出現某種相似的、虛偽飄忽的深情,只不過瞿錦辭從來不屑掩飾,而宋易勛已經太過老成。
“這是我的一位故人。”宋易勛說,“我找了很多畫師來還原她的模樣,可惜總跟記憶里有些出入。”
他不著痕跡地收斂目光,看向寧知蟬。
寧知蟬有些緊張地避開他的視線,同時聞到密閉空間內漂浮的、較為淺薄的沉香木信息素的味道。
宋易勛有些落寞地說:“其實我有時覺得,你和她有點像。”
他走近了些,緩慢地抬了抬手,似乎想要觸摸寧知蟬的面頰,寧知蟬警覺地向后退,沒給他碰到,宋易勛便放下了手,但頑固地繼續靠近寧知蟬。
“知蟬,不要怕。”宋易勛幾乎把寧知蟬逼近角落,聲音很輕地說:“其實叔叔很喜歡你。”
寧知蟬退無可退,周圍沉香木信息素的味道逐漸濃郁起來。
“宋叔叔!”
他用力推開了宋易勛的肩膀,逃到靠近門口的位置。
口袋內的手機適時震動起來,寧知蟬的手輕微發抖,拿出手機,“宋叔叔,我要接個電話。”
屈吟的聲音從聽筒傳進寧知蟬耳朵里:“知蟬,知道今晚你輪休,但有個妹妹臨時有事,你要不要來充個數啊。”
寧知蟬緊緊握著手機,像抓緊救命稻草,看到宋易勛站在原地沒有動,于是盡可能冷靜地對屈吟說:“嗯,沒事,我馬上就過去,你別擔心。”
“什麼擔心?”屈吟頓了頓,很快警覺起來,“知蟬,你那邊出什麼事了嗎?”
“我很快就到,見面說,我先掛了。”寧知蟬掛斷了電話,對不遠處的宋易勛說:“叔叔,我朋友突然出了點急事,我要去看看她的情況。”
“哦,好啊。”宋易勛的聲音恢復了往常的溫和,對寧知蟬笑了笑,走了過來,“你到哪里去,叔叔讓司機送你。”
“不用了叔叔,我可以自己叫車去。”寧知蟬向后退了一點,用力握住門上的把手,但門依舊緊鎖著,沒有打開。
“這里位置比較偏,叫車不太方便,萬一出意外就不好了。”宋易勛伸出手,在墻壁上的電子鎖上掃描了指紋,幫助寧知蟬打開了門,“還是叔叔送你吧。”
寧知蟬不確定宋易勛口中的“意外”會是什麼,也沒辦法跟宋易勛撕破臉皮,于是點了點頭,跟宋易勛走出了房間,再次坐上他的車子。
宋易勛和寧知蟬一起坐在后排,不過沒有說話,也沒有像方才一樣過分靠近寧知蟬。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