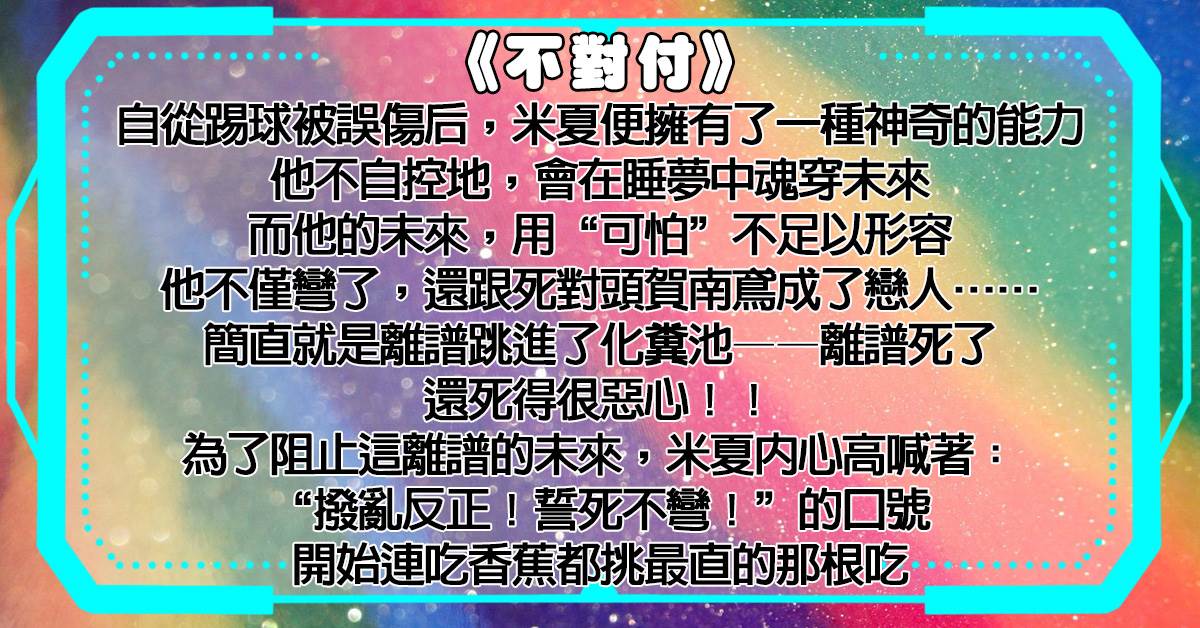《不對付》第95章
“你知道他們這邊有溫泉吧?我們和政府其實一直想要推進層祿族的旅游項目,將這里打造成一個風景優美、老少皆宜的旅游景區。可因為種種原因,這些年始終沒談下來。”說罷,嚴初文嘆了口氣。
“為什麼談不下來?”
“和信仰有些關系。”嚴初文扶了扶眼鏡,道,“他們認為滄瀾雪山上的一切,水、草、石頭,都是山君賦予的。他們可以為了生存去喝山上的水,讓牛羊吃山上的草,用山上的石頭蓋房子,但是不能因為想要財富就出賣山君給他們的東西。”
乍一聽,好像沒毛病?
“其實我看他們好像也不是很缺錢,如果不愿意的話,那就隨他們?”
莫雅她家住在別的村不知道,就看左勇家,不說大富大貴,但也是有車有房,家里三個小孩兒都有書讀,一派安居樂業的景象。跟海城那種大城市肯定沒法比,不過跟我想象中住木屋、沒有水電的景象比還是要好得多。
“那只是棚葛。我剛來這里的時候,棚葛只能接收到一家通信公司的信號,到去年才增加到兩家。你看到的一切安居樂業的景象,都是這一代頻伽花了八年才做到的。但頻伽能輻射到的范圍是有限的,更遠的地方,像那些邊緣的小村寨,他就無能為力了。”嚴初文耐心地解釋道。
“有很多村子,進出只有一條非常危險的山路,一到下雨就有可能引起山體滑坡。那里的孩子上學需要翻山越嶺,起早貪黑,那里的大人,一年辛苦耕種可能也就只夠溫飽。想要這樣的村子富起來,就必須修路,可是修路又要很多很多的錢。
”
這樣一說,當初做第一個夢的時候,未來的我到厝巖崧找賀南鳶,好像就是因為一直下雨差點沒見成。后來賀南鳶冒著風險趕來見“我”,“我”還罵了他一通。
“我明白了,層祿人現在的好日子,是因為頻伽和政府,不是因為山君。”信仰或許能帶來精神上的富足,但帶不了物質上的富足。
嚴初文笑了笑,對我做了個“噓”的手勢:“這話你可不能當著層祿人的面說。”
我說:“沒事,我要說也只會當著賀南鳶的面說。”
可能身體里有一半夏人血統的關系,讓他在層祿族總是缺少歸屬感。雖然他是山君虔誠的信徒,信仰著那些善的、好的,但也是糟粕的反抗者,無比嫌棄著那些后來人強加上的定義與束縛。
我斜倚在二樓陽臺的護欄上,眺望著遠方的滄瀾雪山。雪白的山頂在陽光的照耀下顯得越發神圣不可侵犯,據說至今還沒有人能征服這座圣山。每當有攀登者試圖登上她,層祿族人便會向山君祈求降下風雪。
這個民族,看著與世無爭、無欲無求,但細細接觸起來,其實在人性的復雜多樣上,與夏人也沒什麼區別。
為了不讓我跟賀南鳶單獨相處,舅舅可謂煞費苦心。
先是讓黎央白天的時候跟個小尾巴一樣到處跟著,再是以輔導功課為由,把我們仨一起集中到他屋子里做作業。
我還不能有意見,一有意見,他就用那種明面上客客氣氣,實則暗藏機鋒的語氣問我上學期期末考了年級第幾名。
聽嚴初文說,舅舅當年是首都大學肄業。
首都大學作為國內數一數二的高校,能考上的都不是一般人,我這個193名在他面前都不能算學渣了,應該算智障。
恍惚中,我有種外地窮小子被丈母娘嫌棄一窮二白學歷還低的錯覺。憋屈,但是毫無辦法。我總不能拉著舅舅的手跟他說:“舅舅,你別看我現在不怎麼樣,我將來可是個博士!”
好在賀南鳶很會見縫插針,只要舅舅一走開,就會用腳踢踢我,或者在桌下扯我的袖子,等我將手放到桌下,就一把握住。
寒假最后一禮拜,我就這麼在白天做作業,晚上和賀南鳶幽會中度過了。別說,還挺充實。
離開學還有二天的時候,柏胤說他來送我們去學校,我簡直是歡奔亂跳地收拾了行李。終于啊,我內心載歌載舞,終于能結束這漫長的“異地戀”了!
車上播著音樂,賀南鳶靠在一旁睡著。我吃著嚴初文臨走前給我塞的特產牛肉干,有一搭沒一搭地跟柏胤聊天。
“叔,你什麼時候回海城啊?”
“再過幾天吧。”柏胤唇邊泛出一種帶著柔情的笑意,道,“想多陪陪你們舅舅。”
喲,這是裝都不裝了,攤牌了?
我瞟了眼身旁沒有蘇醒跡象的賀南鳶,小聲問:“舅舅是不是不喜歡我?”
自從知道我跟賀南鳶在一起后,他就一點不親切了,對我好嚴厲啊。
柏胤道:“沒有,他對在意的人才會有脾氣。一般人看他只是頻伽,層祿的言官,親近的人看他才是摩川,是真正的他。”
有他這句話我放心不少。
兩百公里,上午出發,下午也到了。柏胤急著趕回去,晚飯都沒吃就走了。
學校食堂還沒有開,我就跟賀南鳶去老街上逛了逛,買點開學要用的學習用品,再吃個飯。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