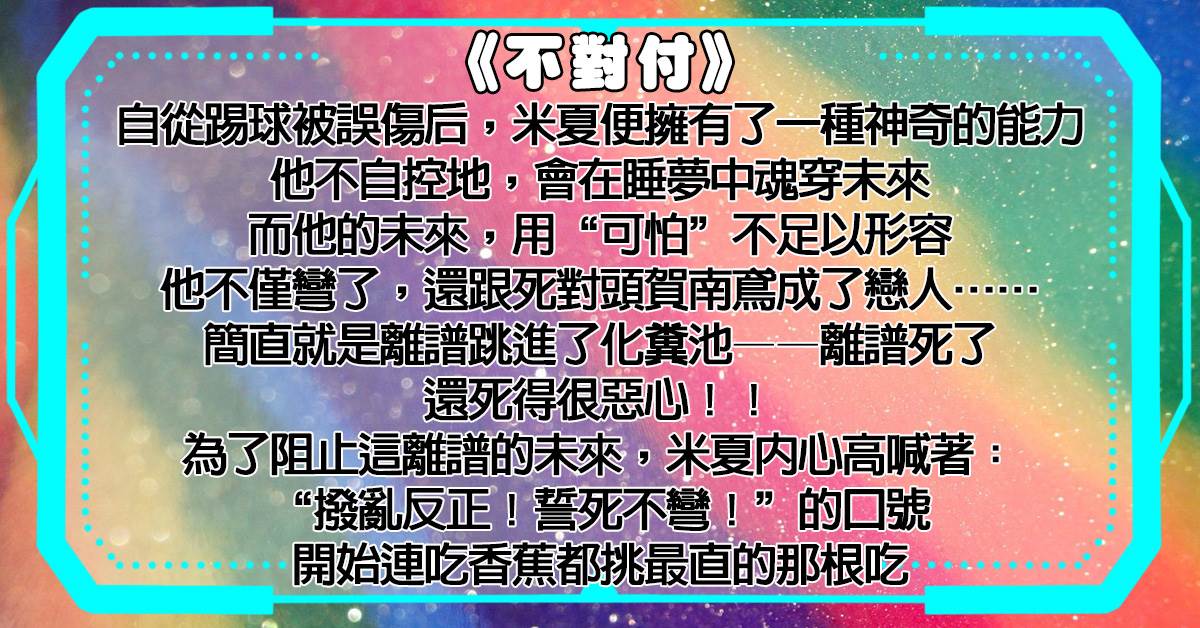《不對付》第80章
再醒來已經天亮了,陽光透過單薄的窗簾照射進來,刺得我眼睛生疼。
我瞇了瞇酸脹的眼睛,想要起來,卻發現自己身體異常沉重。
怎麼回事,是高反了嗎?我怎麼起不來?
被子下摸索著自己的身體,胸口橫著一條胳膊,腿上壓著另一條腿,完全把我壓得動彈不得。轉頭看向一旁,賀南鳶抱著我睡得香甜,絲毫沒有要醒來的趨勢。
一回生二回熟,我現在也是處變不驚了。
輕輕拿開他的手,我坐起身,再是抽出自己的腿下了床。屁股才要離開床鋪,腰上突然一緊,被身后的人一胳膊勾了回去。
我嚇了一跳,以為是賀南鳶故意的,按住他的手回頭瞪了他一眼,結果人壓根沒醒,眼皮都不帶張一下的。
他小時候是遭受過什麼生存考驗嗎?舅舅是不是大冬天不給他蓋被子從而磨煉他的心性了?不然怎麼入睡后對床上的東西這麼有獨占欲的?
好不容易掰開賀南鳶的手,我穿上衣服下了樓,黎央已經起來了,正在給供桌上的鮮花換水。
“早飯在桌上。”他抬抬下巴道。
“好,我刷個牙就來。”
走出小樓,我往洗手間走去,經過主屋時,刻意地回避了視線。雖然知道柏胤這個時間肯定已經走了,但還是好尷尬啊,尷尬得都不敢往那個方向多看一眼。
吃過早飯,賀南鳶還沒起來,我閑來無事,在廟里四處晃了晃。這一晃,不可避免地晃到了主屋前。
主屋是個一層的高大建筑,層高超過十米,一進門就會看到一座鹿首人身的鎏金神像。
鹿王袒露上身,眼含慈悲,雙唇帶笑,耳朵上戴著大大的耳環,胳膊上脖子上全是臂釧、瓔珞等華麗精致的首飾。
看上去……怪眉清目秀的。
鹿王身前供奉著大大小小數十盞酥油燈,鮮花水果也是一應俱全。地上有三個蒲團,應該是供信眾朝拜用的。
我往邊上走了走,神像的右手邊有張小小的書案,上頭擺放著幾本經書。一張宣紙攤在案上,上頭的經文只抄了一半,擱在筆架上的毛筆,筆尖還是濕的。
方向不對,我認紙上的字有點困難,只能歪著腦袋,一字一句往下讀:“……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
什麼意思?
正琢磨著,大概是聽到動靜了,一身白衣的年輕言官掀開簾子從里間出來。
我趕忙直起身,有些變扭地叫了聲:“舅舅,早啊。”
舅舅笑了笑,走到桌案后盤腿坐下,提筆在一張廢紙上寫下一行字遞給我。
我接過一看,上頭說他從今天起要止語七日,這七日都不能說話。
因為受不住誘惑和人在山君跟前那啥了,晚上沉淪,白天后悔,所以罰自己止語七天,凈化自己一切凡心雜念嗎?
這種無意間吃到驚天大瓜的感覺真的好微妙啊。
“哦哦,舅舅你專心修行好了,我……我就是隨便逛逛。”我撓了撓頭,道,“那我不打擾你了,我回去看看賀南鳶醒了沒。”
揮別舅舅,我一路小跑著回到后頭小樓,不知道是因為見了舅舅太刺激了還是跑太快了,心臟撲通撲通亂跳,喘得特別厲害。
賀南鳶已經醒了,正坐在小桌前吃早飯,聽到動靜看過來,視線在我臉上轉悠了圈,微微擰眉:“你跑這麼快做什麼?”
屋里不見黎央,不知道是出去了還是在樓上。
“我剛從舅舅那兒回來,他在止語,說要止七天。”我坐到賀南鳶邊上,端起他的杯子喝了口里頭的奶茶,結果他竟然沒放糖,一點甜味都沒。
“哦,他這半年……經常止語。”賀南鳶咬著手里的餅道。
我咳嗽起來,差點噴他一臉奶茶。
看破不說破,我們倆對視一眼,沒再聊這個話題。
下午,賀南鳶說帶我去巴茲海,那邊風大,讓我多穿點。我斟酌了下,把圍巾和手套都戴上了。
棚葛離巴茲海還有五六十公里,靠兩條腿走肯定是不行的,賀南鳶一早跟左勇說好了,讓他爸爸送我們去。
左勇的爸爸是個黝黑高大的漢子,留著齊肩發和絡腮胡,只會說幾句簡單的夏語,開的是一輛看不出年歲的藍色皮卡。
車上對方一直在跟賀南鳶用層祿語交流,不知怎麼越說越激動,到最后甚至憤怒地敲擊了下方向盤,嚇得我以為他們是吵架了,不安地抓住了賀南鳶的大腿。
賀南鳶低頭看一眼自己的腿,又看了看我,說:“查塔叔是和我媽一起長大的,他在問我去海城找賀明博的事。”
啊,原來是氣這個。
“那你有沒有說我潑賀明博一身咖啡的事?”
坐在副駕駛座的左勇來了興致,回頭道:“你也在場啊?”
“我當然在場了!”我湊上前,宛如說書先生一般,這樣那樣,添油加醋……不是,藝術加工了一番,將我如何看不過去替賀南鳶手撕渣爹的整個過程說給了左勇聽。
左勇聽得一愣一愣的,聽完了緩緩給我鼓起了掌。
“治你們夏人的,還得是你們夏人啊。”
我微微一笑,深藏功與名:“哪里哪里。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