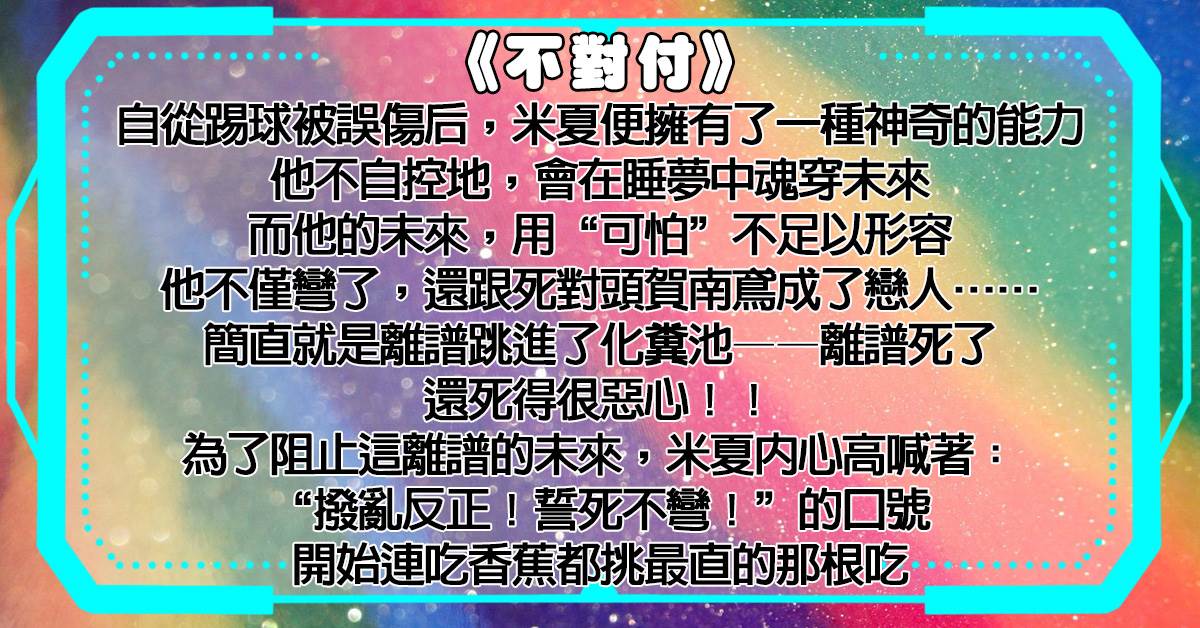《不對付》第43章
“謝謝。”他收下棒棒糖,拆開包裝,當著我的面將它塞進了嘴里。
然后就被酸到了。
“他們真的打算開除你?”我問。
吃又吃不下,丟又不好丟,賀南鳶只得將棒棒糖拿在手里。
“說是最后的決定明天下,今晚還要再討論討論。”
那就好,還沒正式下文件,一切還有挽回余地。
“校長這是慫了。”我夾著嘴里的棒棒糖,就跟夾著支煙一樣,“得逼一逼他。”
賀南鳶看著我,好像已經猜到了我要做什麼,或者也沒猜到,只是覺得我可能要有所行動。
“米夏,你不要亂來。”他認真地,眼里不含一絲笑意地說道。
我重新將棒棒糖含進嘴里,拍拍他的肩:“放心吧,我一個借讀生,他們能拿我怎麼樣?”
晚上趁賀南鳶去洗澡,我跑到陽臺上冒著寒風給米大友打了通電話。自從初中犯了事,米大友就扣下了我所有的錢,包括但不限于從小到大的壓歲錢和我媽留給我的一些存款。我讓他從扣下的錢里撥出幾萬來,想辦法給到一中的校長。
“好你個小兔崽子,我以為你學好了,想不到你丫現在犯罪升級了啊?成績的事是你塞錢能塞好的嗎?”米大友還沒聽我說完就一頓搶白,“再說你一個借讀生,學籍都不在一中你給一中校長塞錢有屁用啊?”
我本來就被風吹得頭疼,一聽他這話,白眼都要翻到天上去:“你有病啊,誰跟你說我是為了成績給校長塞錢了?我敢送他敢收嗎?”
“那你什麼意思?”
我把賀南鳶的事跟他說了一下,著重點明了賀南鳶是我的結對子對象,我成績能夠提升這麼快,對方功不可沒。
“他現在出了事,我能不幫嗎?是你兄弟你能不幫嗎?”
米大友這個人,當丈夫當父親都差點意思,唯獨當朋友沒話說。
“那得幫,一定得幫。”他一聽,比我還要激動,“我明天就找老劉去。”
老劉就是郭家軒的姑父。
我縮著脖子,原地踏步:“也不是讓校長徇私枉法,就是看能不能用錢把這事給了了。能用錢解決的,咱們就別搭上人家的前途,是不是?”
“是是是。”
瞥到屋里賀南鳶回來了,我一下捂住話筒:“那這事就交給你了,你給我辦好了。”
掛了電話,一進屋我就打了個大大的噴嚏。
賀南鳶本來在擦頭發,聽到我動靜停下來,說了一句:“你別又著涼了。”
可能是洗澡不方便,他揭掉了眉骨上的紗布,也讓我得以看清他的傷勢——細細的縫線,大約四五針,截斷眉毛,差點就碰到眼皮了。
要是留疤得破相啊。
“不會,就是鼻子有點癢。”
我當初都沒忍心打他的眼睛,那些混蛋怎麼敢的?我摸著鼻子心想,層祿這幫人還是下手輕了。
之后,我找到左勇的QQ,讓他給我拉了個群,除了洗澡沒辦法操作,其余時間一直在群里激情發言,直到十二點。
第二天起床,我精神飽滿,容光煥發,郭家軒吃早飯時不住打量我,最后忍不住問我為什麼一點都不擔心。
我觀察了下四周,把自己的計劃悄悄告訴了他。
他瞪大眼,半天沖我豎起個大拇指:“義字當頭,情比金堅!”
雖然覺得他用詞有點奇怪,但我還是欣然接受了他的稱贊。
“做兄弟,我是認真的。”
班里的人差不多都知道了周六發生的事,一整個上午班級里都有點愁云慘霧。
我走班上課碰到莫雅,她也非常擔心賀南鳶,不停向我打聽他的情況。
我安撫她:“別擔心,沒事的,我能搞定。”
莫雅眼眸里閃過一抹憂色:“真的能成功嗎?”
顯然,她已經從別人那里得知了我的計劃。
“放心,就算失敗了,有我頂在前面呢。”我沖她微微一笑,盡量展現出自己可靠、穩準的一面。
莫雅點點頭,回了我一個淺淡的微笑。
蓄勢待發了一上午,到午休時,校方終于發力了。
“賀南鳶,左勇,你們出來一下。”王芳站在門口,朝兩人招了招手。
賀南鳶起身欲走,被我扯住了衣服。
他不明所以地看過來,我只是沖他咧嘴一笑:“看我的。”
賀南鳶怔然半晌,蹙眉要說什麼,王芳那邊開始催了。
“賀南鳶?”
賀南鳶煩躁地看了眼門口,回頭匆忙叮囑我:“你別鬧。”說完,抽回自己的衣服,走向王芳。
切!望著他離去的背影,我撇了撇嘴。
我就要鬧。
按照計劃,賀南鳶他們走后,郭家軒和高淼就要去走廊上望風,而我也該閃亮登場了。
我整整衣襟,大步走向講臺,像拍驚堂木那樣用黑板擦拍了拍桌子,示意大家看過來。
“同學們,上周末發生的事,相信大家都知道了……”
我極盡煽動,一字一句,鏗鏘有力,把從米大友身上學來的生意人的那套話術發揮到了極致,鼓動大家反抗不平,對任何一點小惡都不要姑息,不要縱容。
“今天我們沉默了,明天自己遇到這樣的事,別人也會沉默。不要親手扼殺自己的良知,我們是這個國家的希望,是祖國的未來,我們要懂是非黑白,我們要辯忠奸善惡。
我們坐在這個課堂上,學的是禮義廉恥,而不是怎麼像惡勢力低頭!”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