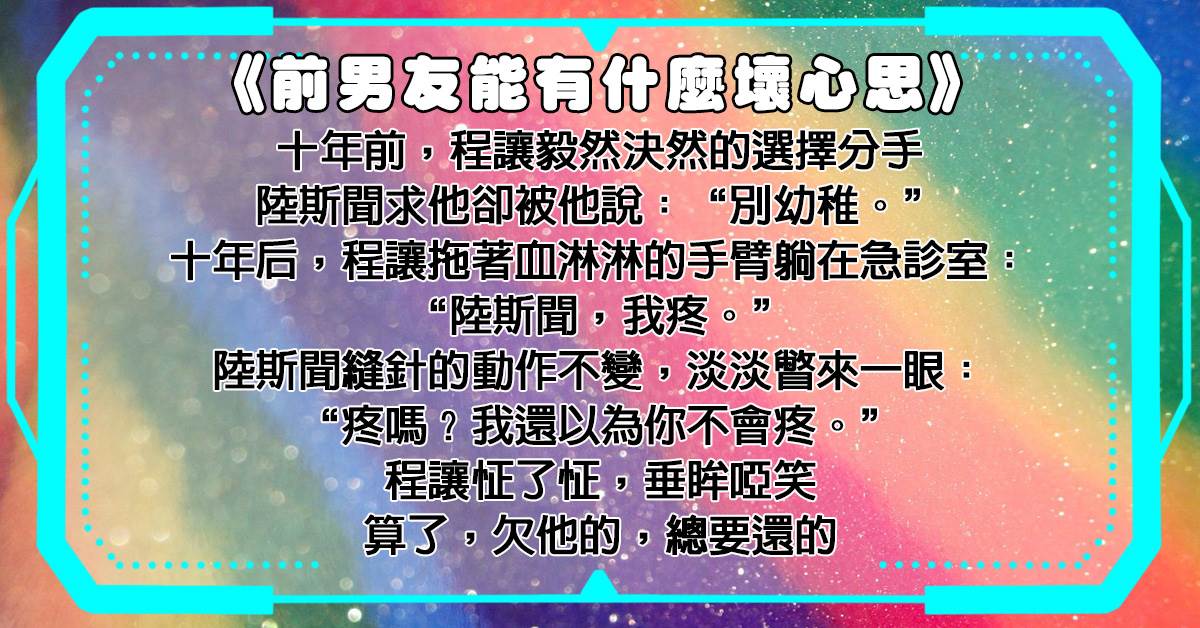《前男友能有什麼壞心思》第28章
車上人很多,程讓被擠在了兩節車廂的連接處,他就靠在門邊的位置,看著車子漸漸駛離月臺,越來越快地朝著北城方向奔跑。
十二個小時的站票,程讓除了去了幾次廁所之外,幾乎沒怎麼動過,就連盒飯都是站在原地吃的,他也不怎麼困,最多也是靠著車廂壁閉上眼睛瞇一會兒,這樣的他近乎有些自虐,可程讓這些年飄來飄去的,趕路是他最習以為常的事情。
而且,他也想看看,看看自己在這漫長且煎熬的途中有沒有一點,哪怕只有一丁點兒后悔想要中途下車的念頭。
可他依然沒有,即便雙腿都站得僵直快要沒有知覺,即便人來人往空氣的味道都讓人開始不適,即便他快要在這嘈雜的環境中待不下去,可他還是沒有下車的念頭,他還是想回去北城,想看一看陸斯聞。
哪怕只看一眼。
近鄉情怯,隨著列車越來越靠近北城,程讓便越來越能清楚地感覺到,但他并非擔心,而是打從心底的畏懼,他畏懼這座城市,畏懼在這座城市里發生的那些事情,他用了十年的時間逃離這個地方,從來沒想過回來。
卻沒想到回來只需要一個沖動。
列車停靠在北城西站的時候已經是清晨4點半,程讓從車上下來踩在地面上的第一步就覺得軟綿綿的沒有真實感。
他回來了。
他居然真的回來這個地方了。
每一步都像是踏在心尖兒上,從月臺到出站口,他把自己的心都踩得麻木了,所以站在出站口看著這座熟悉也陌生的城市的時候才能沒有讓自己看起來過于彷徨和迷茫。
這里曾經是生他養他的地方,他最重要的人曾經都在這里。
可現在,這里已經沒有他的家了。
四點半,天還沒有徹底亮起來,車站旁的小吃店卻已經開始營業,程讓進了一家面館,坐在一層厚厚油漬的桌前吃了小半碗,邊吃邊看朋友圈,陸白沒有更新狀態,程讓便關了手機沒有再看,付賬離開的時候已經五點多,天亮了,這個城市也睡醒了。
或許是時間太早了,程讓并沒有立刻去附屬醫院找陸斯聞,他先是找了一家花店買了一束白菊然后打車去了墓園。
距離上次過來已經十年了,時間久遠的程讓已經沒有什麼記憶,他原本以為自己會忘記賀青的墓在哪里,可他沿著臺階而上的每一步都是有方向的,原來那些以為自己已經遺忘的,從開始到現在一直都在記憶中。
只是被他藏了起來,從不輕易示人罷了。
賀青的墓碑在半山腰,程讓沒走一步冤枉路的在幾分鐘后站在了她的面前,墓碑被清掃得很干凈,大概是有人經常過來看她,程讓靜默幾秒將白菊放在了她的墓碑前,在沉默蔓延了許久之后,程讓才輕聲說了句:
“媽,我來看你了。”
十年未見,理所應當的有很多話要說,可這天程讓在墓地待了許久,但自始至終也只說了開頭的那一句,便再也沒有別的聲音,他不知道要說什麼,也不認為說什麼賀青還能聽得到,已經走了那麼那麼久了,即便有輪回賀青也已經有了一個新的開始。
一個嶄新的人生。
墓碑留在這里不過是給活著的人一個寄托。
可程讓不覺得自己有什麼需要寄托的,賀青也不該再有誰拖著她了。
或許是連續趕路太久沒睡了,程讓竟靠著賀青的墓碑睡了過去,等他醒來的時候已經臨近中午,這是自和陸斯聞分開之后難得的一個沒有夢的覺,是媽媽給他的。
他起身回頭看了一眼賀青,緩緩笑了笑,然后連句再見也沒有說便邁步離開了。
上次分開是十年,這次或許會更久,實在也用不著再見。
沒有打算多留,原本應該看一眼陸斯聞就走,可在車上擠了十幾個小時,胡子拉碴連衣服都有了味道,說服不了以這樣的模樣去見陸斯聞,程讓找了家快捷酒店,等收拾好自己出門的時候才發現已經快五點了,醫院也已經下班了。
即便現在去找陸斯聞,怕是也見不到了。
已經過去十年了,如今連陸斯聞住在哪里他都不知道。
只能等明天。
程讓在床尾坐下,手肘撐著膝蓋低著頭,維持了這個姿勢很長時間,沒有人知道他在想什麼,直到窗外的天色漸漸暗下來,他才抬起頭看了一眼,然后又去浴室洗了把臉,拿上手機和房卡出門了。
對于這座熟悉卻離開了很多年的城市,程讓沒有半點心思去看看它的改變,他只是出來吃點東西,吃完就回去。
北城這座城市本不小,如果刻意避開,同在這座城市的人一輩子不碰一面也是可以的,但北城又很小,小到程讓只是出來吃點東西就能和陸白撞上。
程讓沒刻意挑店面,他對這方面本就沒有要求,不餓就行,距離酒店最近的是個大排檔燒烤,程讓點了些烤串找了個角落的位置坐下來,視線落在旁邊人來人往的街道上,眼神是茫然的。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