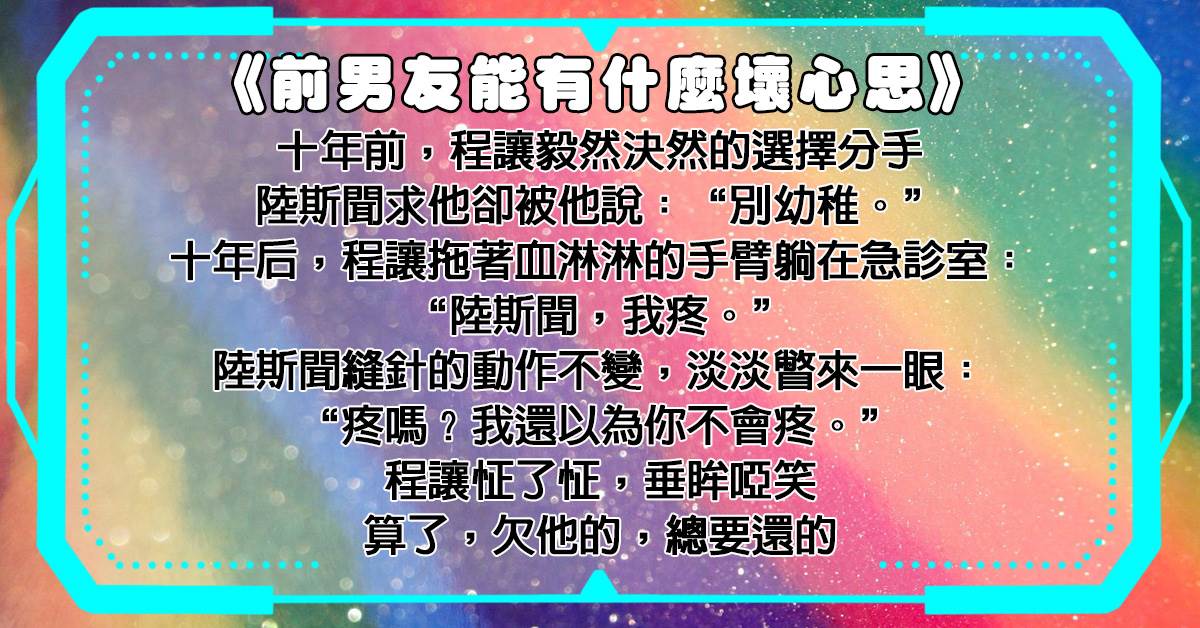《前男友能有什麼壞心思》第26章
如果被證實,那麼他又該怎麼做?
他又能做什麼?
陸白沒有接聽,程讓緊接著打了第三個,第三個語音通話電話屏幕上也顯示出‘手機可能不在身邊’字樣的時候,陸白才終于接聽了電話。
不知道發生了什麼,語氣有些吞吞吐吐:“程讓哥,這麼晚了,找我有事兒啊?”
程讓沒有繞彎子:
“我看到你朋友圈了,怎麼回事?陸斯聞的手怎麼了?”
“朋友圈?什麼朋友圈?我沒發。”陸白的語氣有些緊繃,像是被誰監視威脅著,語氣也帶著點戰戰兢兢:“你看錯了程讓哥,我都睡著了,你沒別的事兒我掛了。”
說完不等程讓有什麼反應就直接撂了電話,程讓幾乎是沒有猶豫的再次撥通了過去,但接連幾次都沒有人再接聽了。再去翻看陸白的朋友圈,之前發的那條果然已經被刪除了,這一切荒唐的好像只是程讓的幻想。
可是就算是幻想,又怎麼會幻想陸斯聞的手無法手術,別說陸斯聞,這也是程讓不能接受的事情。
那陸白為什麼不承認?
雨漸漸小的時候程讓也冷靜了下來,陸白剛才的語氣一直在吞吞吐吐,像是被威脅著,如果他的身邊真的有人也不可能是別人,沒有誰能管到陸白跟自己說什麼,發什麼朋友圈,唯一的可能就是陸斯聞。
兩個人分開時候吵的那次架程讓明里暗里的都說過不想再欠他更多了。
陸斯聞是生氣了,可他還是不想讓程讓覺得欠他更多。
即使以后都不能再手術。
即便那麼那麼生氣。
他傻不傻?為自己想這麼多做什麼?自己什麼時候領過情?他到底知不知道自己根本不值得他為自己考慮這麼這麼多。
程讓不知道在窗前站了多久,等他回過神的時候雙腿都已經近乎僵直,雨早就不下了,程讓推開窗,雨后清新的空氣夾雜著絲絲涼意撲面而來,那不顧一切想要回去北城看陸斯聞的沖動也像雨后春筍般勢如破竹。
他快要壓制不住。
陸白發這樣的朋友圈應該就是已經確定了的,不然也不會公之于眾,在此之前不管是陸斯聞還是他的家人也一定是做了很多很多努力的。
程讓回去能做什麼呢?他不是醫生,他什麼也改變不了什麼的。
他不可能讓陸斯聞的手好起來。
他甚至安慰的話都不知道該怎麼說。
陸斯聞不能手術了,這對于一個外科醫生來說,這意味著什麼?陸斯聞是什麼感受?程讓不敢想。
他真的是個災星,真的是個禍害,陸斯聞怎麼就這麼倒霉,偏偏遇上了自己?
所以回去做什麼呢?什麼忙都幫不上,或許還會給他帶來新的災難,自己永遠不出現在他的面前就是對他最好的方式了。
他就該距離陸斯聞遠遠地。
越遠越好。
酒吧的門就是這個時候被推開的,程讓沒聽到,意識到有人走近的時候他才抬起頭剛想說一聲‘不營業’,可話還沒說出口,就愣了一瞬,有些詫異地看著眼前的來人:
“焰哥,已哥,什麼時候回來的?”
焰哥名叫遲焰,他是這家酒吧最開始的老板,已哥名叫顧已,是遲焰的愛人,他們已經離開兩年多了,程讓沒想到他們還會回來。
“自駕游,順便過來的。”遲焰笑看著程讓,視線在酒吧內掃了一圈:“不做了?”
“嗯。
”程讓應了聲:“準備離開了。”
幾人在吧臺前坐下,遲焰笑看著他:“已經比我預想中的時間要長得多了。”
程讓聞言愣了一瞬,隨即淡淡一笑:“我看起來這麼沒定性嗎?”
“如果你見過第一次走進這個酒吧時候的自己,你也會這麼覺得的。”遲焰說完看了一眼顧已,笑了笑。
程讓沒問自己當初在遲焰和顧已眼中是什麼模樣,沒有人比他更清楚,他本就是無根浮萍,飄到哪里算哪里,接下這個店面起初是為了幫忙,覺得遲焰和顧已還能回來,后來回不來說送給自己的時候,程讓覺得飄了這麼多年,試試也無妨,但他始終對這里沒有任何的歸屬感。
事實上,這個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地方可以給自己歸屬感。
他總是從這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已經習慣了。
程讓拿來了店里剩下的最后幾瓶酒,顧已要開車,沒喝,遲焰和程讓有一搭沒一搭地喝著,兩瓶酒空了遲焰要去開第三瓶的時候卻被顧已搶了過去,放在了旁邊:“不許喝了。”
遲焰笑看他:“已哥,這點兒酒不是我的量。”
“嗯。”顧已認可地點點頭,又問他:“那上周喝醉酒第二天頭疼的時候是誰要我看好你以后不再喝多的?說話不算話?”
程讓坐在他們對面看著遲焰近乎撒嬌一樣的勾了勾顧已的小拇指,而顧已就那麼握住了他,緊緊的。
遲焰轉頭看過來的時候就看到程讓這樣的目光,帶著點羨慕的同時也有點疑惑,似乎不太明白。
“羨慕啊?”遲焰敲了敲桌面讓程讓回了神:“找一個啊。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