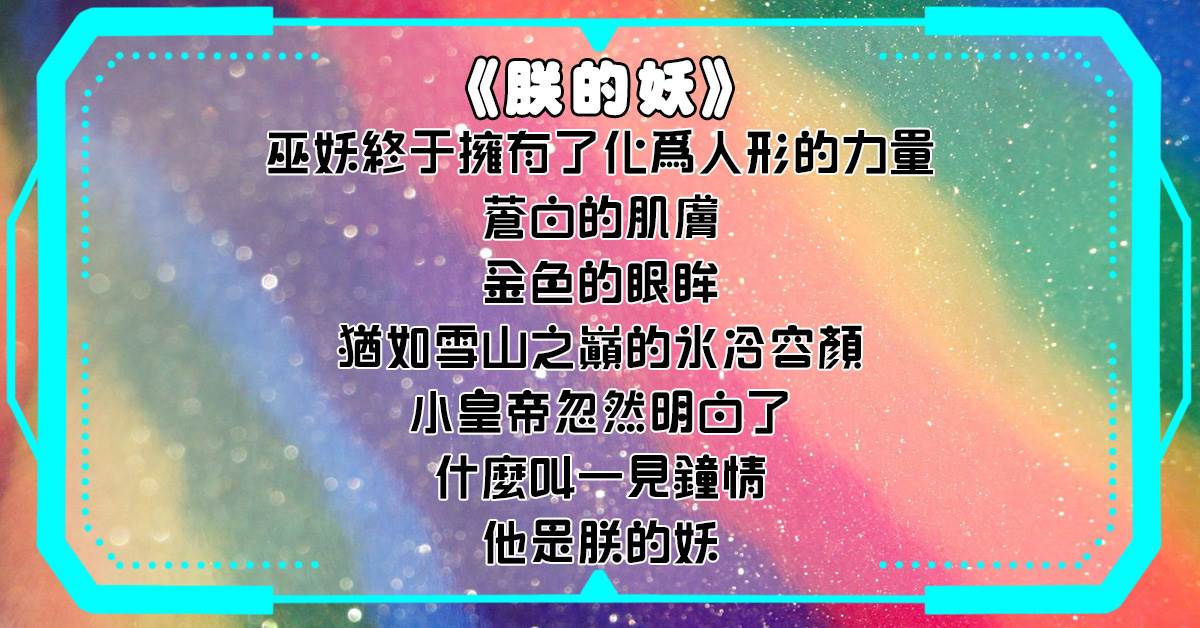《朕的妖》第253章
”
青光大盛,無數的光澤猶如春陽一般,吹出徐徐暖風,女媧的虛影淡淡在天地之間,猶如從前補天一般,傲然頂天立地。
蕭偃看著她,神容悲憫:“朕身上的,是九州山岳臺布下的山川地理陣給予的山海自然之力,你還沒發現嗎?你的山河社稷圖,已經變成這座山河大陣的陣眼了,上古女媧留下的神器,果然可堪為陣眼。以身補天的女媧,豈會將神器任由你這等竊取神器的貪婪小人操縱?”
鮮于鸞道:“你胡說!我可是星官圣女,唯一的女媧傳人!”她聲音里其實帶了些慌張,驅動蛇杖,然而那卷山河社稷只是微微展開著,光芒大盛。
無數金色的光點,不知從何處被風吹來,彌漫在祭臺之上,
“來時無跡去無蹤,去與來時事一同。何須更問浮生事,只此浮生是夢中。”
金發巫妖忽然緩緩睜開了眼睛,金眸璀璨,他在光球里站了起來,微微環顧身周,顯然注意到了山河社稷圖結界里的變化。他皺了皺眉,輕而易舉地從光幕中穿行出來,光幕如同水波一般,柔順地展開,巫妖踏上了祭臺,然后第一時間注意到了祭臺滿地的血,以及躺在那里生息全無的帝王。
他微微抬頭,目光與空中的青年帝王眼神觸及,烏云朵已倏然閃現回來,瞬間將發生的一切共享記憶給了巫妖。
了然一切的巫妖不敢再看帝王的哀慟漠然的眼睛,緩緩走到了祭臺上,跪下將那具渾身血污的帝王身軀,慢慢抱入了自己懷中,席地跪坐,輕輕將帝王的身軀抱得更貼近自己,低頭吻了吻那閉著眼睛冰冷蒼白卻仍然充滿了倔強的面容,又伸出手掌按住那胸口尚且還在涌著血的致命傷口,低低嘆息道:“真是……太倔了……”
青年帝王的虛影懸在半空中,垂眸看著他,神情冷漠:“你總是瞞著我,哄著我……”
金發巫妖抬眼看著他,神情充滿了無可奈何:“冰窖里的冰棺,原本是要填入山川地理陣,作為陣眼。但是——每一次你看著我,都仿佛透過我看著過去記憶里的帝師,半魂消散后,那具魂體就會蘇醒,你更希望那個有記憶的帝師回來吧。你想要江海相期煙霞相許的,是你的先生。”你還把寓意結發的發絲也放進棺材里了。
青年帝王微微抬了眼皮,看了他一眼:“朕都要。”
金發巫妖:“……”
他忽然似有所感,抬眼看了下虛空中,有些意外:“怎麼醒了?”
無盡的虛空中,雪花漫天飛舞,巫妖分魂現身,冰涼的白骨鎖鏈與無數靈魂寶石鑲嵌著的華美法袍在空中飛揚著,千年的巫妖分魂伸出纖長骨手拉開了魔法斗篷,露出了胸口一個穿心黑洞:“靈魂契約。”
原來蕭偃給自己刺的那一劍,本體在山河社稷陣里,被隔絕在了小世界中,沒有分擔到,卻被這具魂體分擔到了傷害,于是從沉眠中赫然驚醒。
他重新拉回斗篷,雙眸燃燒著幽白的魂火,問另一半分魂:“為什麼不按原定計劃行事?”分魂剛剛從沉眠中醒來,與本體共享了記憶,滿地觸目驚心的血讓他又驚又怒,對自己的怨恨和懊惱達到了頂峰。
抱著帝王身軀的巫妖本體沒有說話,只又看了眼青年帝王猶如霜雪一般寒冷的臉,另外一半分魂終于感覺到了伴侶那含而不露的帝王之怒。
此刻,急需一個轉移注意力的倒霉鬼,本體和分魂心有靈犀都看向了鮮于鸞,分魂揮舞著骨鏈,千百道帶著冰霜之力的骨鏈,仿佛帶著來自不死深淵千萬幽魂的嚎哭尖嘯,穿過那女身蛇尾虛影!
虛影在骨鏈觸到之時,就已消散開去,鮮于鸞催動山河社稷圖發現果然再也無法驅動,連連揮手想要施展隱術,然而一個冰霜骨刺牢籠從地上忽然冒了出來,將她困在了里頭。她握住冰冷的骨刺,不甘地坐到了地上。
分魂看向天上,卻見那黑龍已杳然無影,青年帝王的虛影也已消失。
巫妖抱著帝王的身軀,一邊給他喂著治愈藥水,一邊低聲道:“神魂歸位,消耗太大,加上身體損耗太嚴重,得立刻給他醫治。”
分魂金眸冰冷:“執行力太差,本可以完全可以避免這一劫,你該按原計劃將冰棺放入陣眼,女媧的神器并不見得效果更好。”
巫妖寒聲道:“他說,他都要。”
分魂垂下了眉眼,心里涌上了愧疚。身周淡藍色的符文微光泛起,魂體由實轉虛,變成了暗黑色的影子,走向巫妖本體,身影重疊,黑暗主君神魂合一,他感覺到了從未如此的完整和強大。
而天地間充滿了靈氣,虛空澄凈,他不再被法則排斥。
他單膝跪下,抱起了他的帝王伴侶,新誕生的秩序之神,新的世界法則制定者。
作者有話要說:
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國則受命于君。——董仲舒《春秋繁露》
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荀子·天論》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