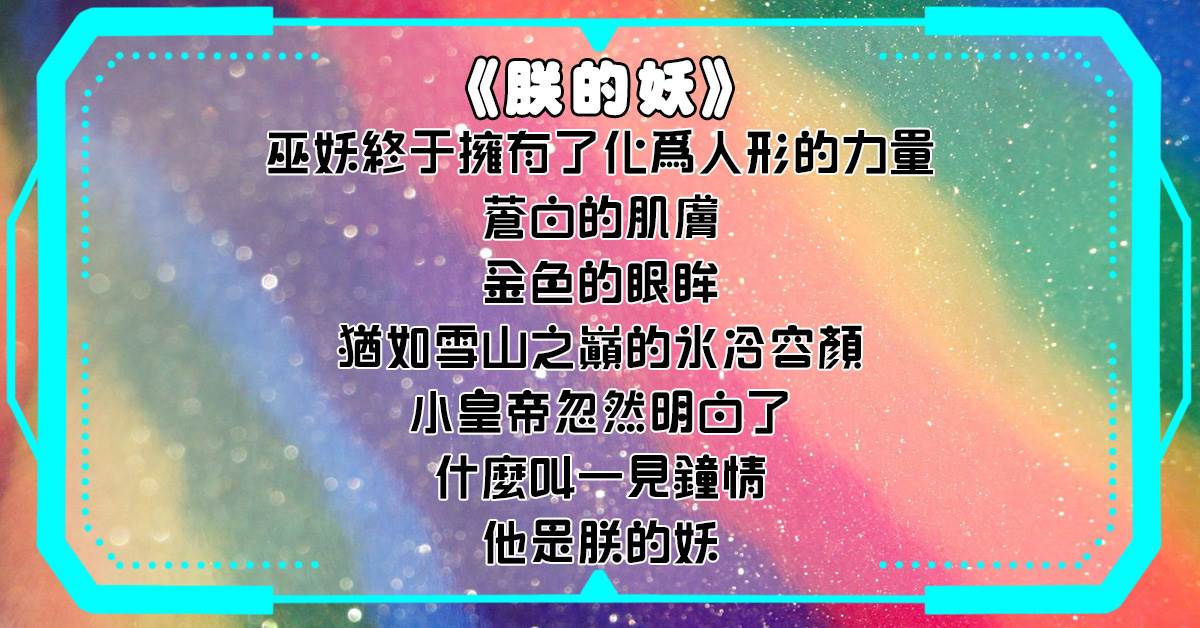《朕的妖》第206章
他大吃一驚,卻看到被骨鏈穿刺的菩薩金像寸寸皸裂,露出了里頭的石胎來。
他失聲問道:“帝師?”
香煙裊裊中,祁垣也語塞了,只看到大殿中平地卷起霜風激烈,金像片片落下,金像下的石像面容露了出來,竟然是一名少女,頭戴華貴鸞鳳冠冕,身穿華麗裙袍,腳下踏著的鯉魚,卻已脫去外殼,只看到一頭形似老虎,卻生著雙翼的野獸!
他終于忍不住問道:“這是誰?觀音像如何變成了這個女子?”
巫妖淡道:“北狄圣女,鮮于鸞公主。”
祁垣語塞:“鮮于鸞?這是普覺國師的妹妹?他為什麼要將自己妹妹的石像供奉在這里?”
巫妖道:“收集信仰之力,也就是你們說的收集人間香火。普覺國師這一招已是駕輕就熟了,當初我就覺得奇怪,你們有名有功德的和尚也不少,如何就他有些信仰之力,想來是家傳有些本事,能夠想法子把信仰之力收集成為自身法力,但偽神終究是偽神,這種法子收集的愿力和信仰之力,終究無根之木無源之水,一次性的。”
巫妖一揮衣袖,那鳳冠少女石像砰的一下炸成無數石粉。
祁垣尚且不知所措,巫妖又道:“那放生池,填平換個地方,我猜他們之前就是把那長翅膀的畜生放在里頭,收集吞噬善念愿力,里頭已被污染,用不得了。”
祁垣道:“愿力也能吞噬?”
巫妖道:“憐憫、戒殺、祈福,無論是否是功利之心,許多人那一剎那放生的行為含著善念,有的則寄托著很強的愿力。”
祁垣若有所思,巫妖已走了出去:“回去了,耽誤了我太多時間了。
”
話音才落他已融化入了漆黑的夜里。
祁垣本來還想多問幾句,看他如此忙碌,也只能回去禪寺內,將被魘鎮住的僧人們一個個喚醒,收拾大殿內的殘骸,打發人填平放生池,重塑觀音像。
巫妖卻剛剛回到京城內,一眼卻看到宮城上空怨氣沖天。
他有些舍不得蕭偃,但還是轉頭去了宮城內。
漆黑的夜里,嬰兒哭聲越發大而清晰。
白骨領主手持著漆黑的劊子手之刀,一刀將一個鬼胎劈成了兩半,那鬼胎分成兩片,卻仍然在地上蠕動著,張開嘴嗷嗷哭著,越發凄切詭異,漆黑的怨氣從鬼胎身上生起。
巫妖站在屋檐下往下看去,心里想著倒是剛才應該把祁垣帶來,把這鬼胎給超度掉,那和尚情劫已過,佛心已成,這鬼胎身負罪孽怨氣,又是懵懂嬰靈,被人故意將胎兒保存下來引發了其中的邪怨,以至于成為強大的鬼怪。
那北狄,似乎有什麼養鬼御妖的法門,但按此世界法則,行此違反天道之事,只會受到天道和法則的反噬,付出的代價應當不小。卻不知那北狄公主,用了什麼作為獻祭的代價了。
看到另外一側甘汝林手持著雙手白骨巨劍,劍風凜冽,與高元靈戰在一起。
那高元靈身如鬼魅,面如金紙,忽然大喝一聲,身上爆發出一陣沖天煞氣,把那高元靈震得面色慘白,渾身動不了,然后千鈞一刀斬下,只看到骨碌碌,高元靈的頭顱被斬下,然后在地上滾了好幾丈。
那頭顱在地上滾了滾,面容憤怒,忽然張開嘴嚎叫起來,發出了尖利的聲音。
甘汝林卻面無表情,上前繼續一刀,將那無頭的身軀繼續一刀斬成兩半。
那頭顱發出了尖嘯聲,然后頭上長出了彎角,慢慢變成了一個羊形的怪物,卻仍然有著高元靈的臉,四只足仍然像人的足一般,他張嘴繼續嚎叫著,看著牙齒尖利如猛獸牙齒,聲音就如同嬰兒啼哭一般。
他一哭那嬰靈也跟著他一起哭起來,一時庭院中鬼泣森森,嬰啼詭譎。
巫妖站在上頭嘖了聲,覺得實在有些不符合自己的審美。
只看白骨領主一揮袖已浮在了空中,張嘴開始放出清歌,聲音緩緩如同母親喁喁低語,哄唱著搖籃中的嬰兒,妮妮噥噥,溫柔萬千,慈祥親近。
只看到那嬰靈哭聲漸漸小了下去,仿佛嬰兒被哄睡了,偶爾哭噎一兩聲,那羊身人頭的怪物也抵擋不住,慢慢伏趴下去,仿佛睡著一般,顯然是比較低級的鬼物。
白骨領主一邊輕聲唱著,一邊慢慢提著劊子手之刀走過去,這次刀上凝成了幽藍色的光,一刀斬下,那嬰兒在甜夢中變成了一個漆黑的光點,慢慢浮起,然后凝結成一塊金色的靈魂寶石落了下來。
而另外一邊甘汝林也已一刀再次斬下了那高元靈的頭,此物黑霧纏繞,同樣變成了一塊豐碩的紅色靈魂寶石。
白骨領主上前捧起那兩顆靈魂寶石過來,跪下奉與巫妖:“主君大人。”
巫妖搖了搖頭:“你留著自用吧,算你有些運氣,雖說靈智不高,但這對你有好處……恐怕,你能以鬼靈之身,孕育胎兒了。”
白骨領主震驚抬起眼:“什麼?”
巫妖淡道:“以后再和你說,此間事既已了,我先走了。”話音才落,他已倏然消失。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