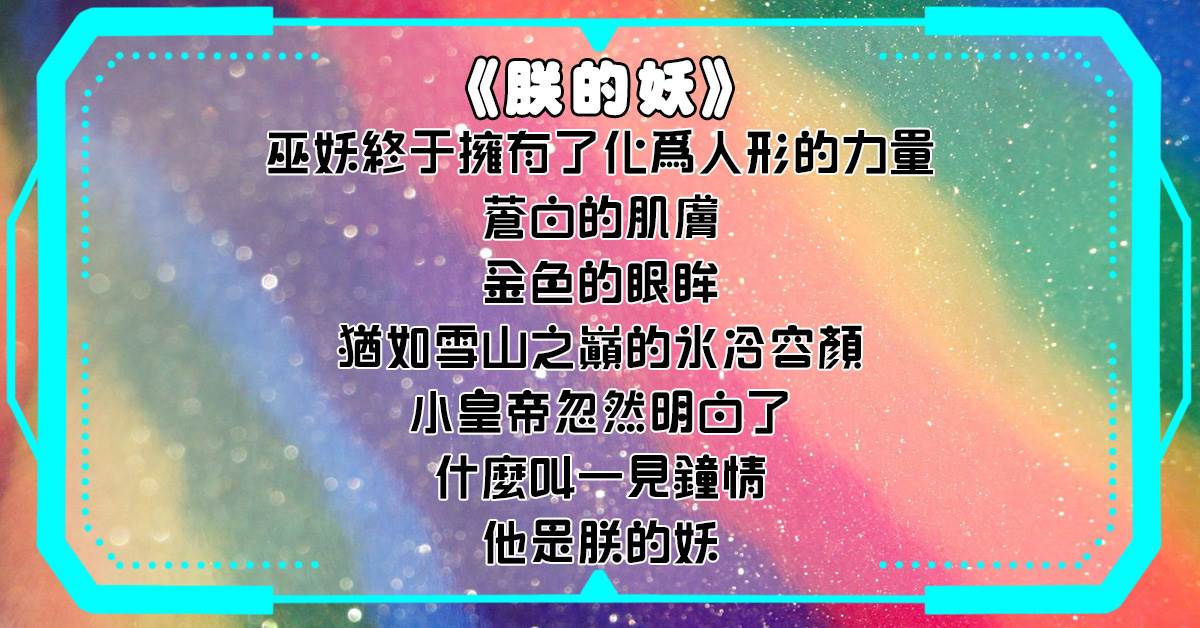《朕的妖》第176章
祝如風道:“別理他,在封地橫行霸道慣了,進了京也不知道收斂點,頭幾年皇上忙著戰事和朝政,沒空收拾他們,如今惹了事出來,豈會縱著他。”
衛凡君道:“皇上英明,不過我覺得老王妃在呢,皇上怕是會念著舊情,算了……”
祝如風笑了聲:“能有什麼舊情。”他想了下又補充道:“先生昨天逛了街,可能累了,昨晚就發起熱來,也沒說,早晨皇上發現的,一大早剛讓人請了江太醫過去了呢。”
衛凡君一聽驚訝又關心道:“啊是不是昨天那只狗嚇到了,還有天氣那麼熱,在臭烘烘的車馬行走了半日,唉,難怪我昨天看巫先生臉色不太好。”
祝如風道:“沒事,江太醫說和之前一樣,神魂不寧,好好歇著幾日,最好哪里都別去,少思少想,靜靜養著就行。”
不過那世子可就慘了,皇上今天發現巫先生在發熱時的那表情可真的是……差點連朝都不上了,幸好隔壁的藥堂買下來了,江大夫就在隔壁,過來得快,把脈后說不妨事,這才黑著臉去上朝了。
不提安國公府雞飛狗跳,津王府這邊津王回了府中,便讓人請了王妃過來,態度非常不高興:“怎麼回事?母妃要進宮,你如何不攔著?如今京城哪個不笑話我們連安國公府都比不過?”
王妃道:“母妃是什麼脾氣您還不知道嗎?她要進宮我能怎麼辦?她那麼寵老二家的那個,聽到被狗咬了,再一聽是因為和安國公府的小世孫,她那唯我獨尊的脾氣,哪里能忍?如今家里也都瞞著她,若是知道連那狗販子都被放了,怕不是連京兆尹府都能帶人去砸了。
”
津王皺了皺眉:“今日皇上召我進宮,話里話外就是責我未能孝敬好母妃,又治家不嚴,未能約束小輩,些許小事就胡亂誣攀,鬧到宮里御前,給人看笑話。我好一番請罪,臉都丟盡了,皇上也不聽我解釋,就讓我出了宮,你是沒看到皇上那臉,可沒念什麼兄弟情分。”
津王妃有些憂慮道:“皇上沒罰您吧?我昨兒是看到皇上臉色不大好,母妃說什麼一門三王爺,還有個皇帝侄兒,還是被人欺負上門,這話一說出來,皇上臉色都變了。”
津王冷哼了聲:“他倒是想和我們撇清干凈,論血緣,誰親得過我們這邊?立太子之時,硬是由著大長公主那邊選了睿親王那邊的小子,他這是忘了自己的根,沒有我們,他能有今天?”
津王妃哪敢說這些,只能道:“當時那是戰事危急之際,不把儲位定了,皇上如何御駕親征呢,再說了當時皇上也說不上什麼話吧。”說起來這位皇上,要不怎麼說英明呢,誰能想到他十六歲力挽狂瀾,硬是靠著一個人死守京城社稷,將這皇位給坐穩了?要不是他坐穩了,他們才有這一門三王,津王妃心中默默吐槽婆婆和丈夫這一副顛倒黑白的論調,還真以為皇上從母妃肚子出來是多大的恩情呢,換個人,現在怕不是偏安在西京繼續做個傀儡皇帝?
看津王還在發泄著怒火:“京里這些世家勛貴,哪一家都水深。早之前進京前,就和你們說過,大長公主府、安國公府,那都是不能惹的,文臣那邊嘴皮子厲害,也不要惹文臣,落人口舌。
只以拉攏為主。我聽說運榮一直老和別人安國公府上的公子過不去,才有這場氣生?”
津王妃道:“當時皇上問我,我答不出來,回來便把平日跟著運榮的倆小廝抓來問了一回,才知道原來是運榮當時才進京,別人不認識他,有次打馬球被衛家那小公子搶了個球,搶了風頭,就記恨在心,后來就一直杠上了。”
津王怒火萬丈:“就這?老二媳婦也不管管他?依我看這狗咬得好!”
津王妃撇了撇嘴,津王道:“罷了,管好咱們家的安榮,別給帶壞了——也別凈去母妃跟前,母妃太寵孫子,寵壞了倒連累了我們。只拘緊了好好讀書。”
津王想了下又道:“這麼辦,你先派人去安國公府送一份厚禮,就說當時事情沒問清楚,冤枉了府上的小少爺,給他賠禮道歉。然后這段時間咱們王府閉門不見客,也不去別人家做客,只說母妃病了,放出風去,說是傷心抑郁,再傳出去老二家那小子腿怕是不行了,可能要耽誤行走。”
津王妃一愣:“為何要這麼做?再說母妃……她待不住吧。”說起來是老王妃,其實也就五十來歲,吃得下睡得著腿腳靈便有氣就往別人身上撒,別人看她是皇上生母,只能忍著,她有時候都覺得說不定自己操勞成疾歸天了老王妃還能痛快再活個五十年沒問題,整日里看戲游園子腿腳利索著呢!
津王道:“呵呵,皇上不是要撇清嗎?他倚重安國公,倚重大長公主府,這事兒,委屈在我們王府!委屈大發了!我們姿態做足了,讓大家看看。
安國公你厲害吧?三朝老臣吧?能把皇上生母給逼得生病了,這權臣仗勢凌人,看看天下人怎麼說!皇上待生身母親,是個什麼樣子,仁孝治天下,這仁在哪里,孝在哪里?他再怎麼說禮法,也抹不平他從咱們母妃肚子里出來,和咱們是同胞兄弟的事實!”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