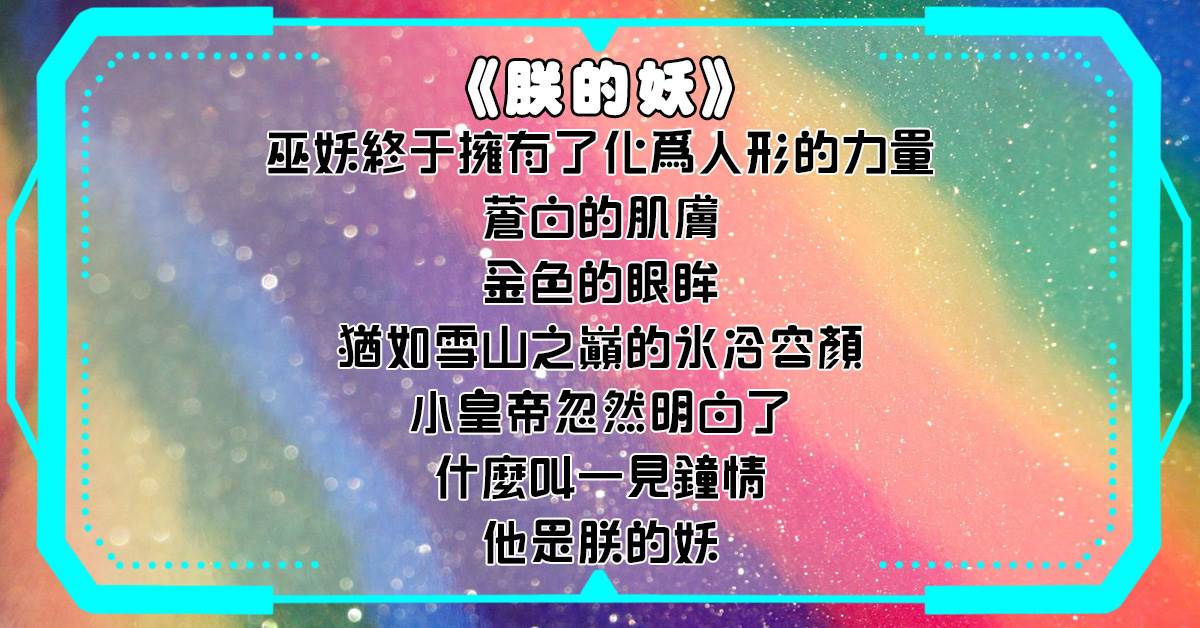《朕的妖》第165章
想到剛才衛凡君那偷偷摸摸遮掩腿上不便的樣子,他就氣不打一處來,還以為他老糊涂了嗎?
小子被祝如風給哄上手了,還遮遮掩掩,想瞞著自己呢,呵呵。什麼一直在宮里,皇上既然在金甌坊,祝如風能不在那里?!
安國公愁眉苦臉想著到底是祝如風把皇帝教壞了還是皇帝啟發了祝如風衛凡君,一邊愁眉苦臉送走了歐陽駙馬,關了大門,對外稱病拒客去了。
金甌坊里安靜靜謐,蕭偃摸了摸巫妖的額頭,看還是滾燙的,在一旁的碎冰水盆里拿了冰手巾輕輕擰了擰,繼續敷上了他的額頭,然后起身在拿了另外個帕子,輕輕揭開被子,將巫妖的手足都用冰水重新擦了一遍,感覺溫度有所下降,才停了下來,拉過那張被子,妥帖蓋上,卻看到巫妖濃密羽睫抖了抖,睜開了眼睛。
他幾乎屏住了呼吸,這三天巫妖也睜開眼睛過,但都是神志模糊認不出人的狀態,而且對什麼都拒絕,藥喂進去才嘗到味道就全吐了,水勉強喝一些,對水要求也很高,略微有點茶葉之類的,便轉過臉去拒絕。
他低著頭凝視著巫妖,看巫妖準確無誤盯著他,金色的眼眸里第一次出現了他的身影,他身體幾乎微微顫抖,他低聲問:“醒來了?好一些嗎?”
巫妖眼睛里出現了一陣迷茫,然后很快又閉上了眼睛,顯然是在掩飾自己的神情弱點。蕭偃心里微微一沉,伸手摸了摸巫妖的額頭,感覺到那里仍然熱著,輕聲問:“你……還是認不出我嗎?”
巫妖閉著眼睛不說話,蕭偃試探著問:“你是不是,記不住過去的事情了?”
巫妖睜開眼睛看著他,金色地眼睛陌生又疏離,蕭偃伸手握住他在枕邊的手掌,心里一陣難過涌了上來,但忍住了仍然在微笑:“你應該受到了很巨大的法術的震蕩,雖然我想象不出,但是你身上的法袍破裂得很厲害,我為你換的衣服……換下來后我試了下,發現那法袍是非常牢固的材料,水火不侵,刀刺不裂,天衣無縫,這樣的法袍,都被撕裂了,可見你遭受了多麼大的法術沖擊。你應該是神魂再次受到了巨大的重創,雖然身體沒有外傷,但是高熱不退,我們……我們這里的藥應該對你沒有用。”
蕭偃越說越難過,低聲道:“雖然不知道如何向你介紹我,讓你信任我,但是……你之前也受過比這更嚴重的創傷,而且你那時候是沒有身體的,我不知道你怎麼再次擁有了身體,不過,也許這個可以讓你信任我一些。”
蕭偃垂著睫毛將掛在胸口的魂匣慢慢從懷里抽了出來,示意給他看:“這是你的魂匣,你能感受到嗎?”
巫妖臉上神色有些意外,伸出手來摸了摸那個魂匣,才慢慢開口:“對不起,你看起來很難過,我想,你應該是我很信任的人,所以我才把魂匣交給你,只是我現在非常混亂,可能需要時間恢復……”
他的聲音柔和動聽,臉上的表情也優雅溫柔,外貌又完全是個雌雄莫辨的少年,與巫妖時候給人感覺的淡漠成熟完全不同,蕭偃握緊他的手,心里的難過無以言表,恨不得大哭一場,但卻仍然維持著儀態:“你好好休息。
”
他彎腰將巫妖抱著起身,拿著旁邊柔軟的枕頭拉過來墊在他身后:“你先忍忍。”
他起身走到一旁的架子上,找出了一個秘銀架子出來,上面擺滿了各種魔法藥水瓶子,五顏六色,他端過來拉在床邊的床頭柜上給他看:“這是你從前離開之前留給我的魔法藥水,興許對你現在的狀況有用,你之前昏迷著,我不敢胡亂給你用藥。”
他對巫妖露出了個笑容,雖然在巫妖看來那笑容仍然十分勉強:“我這些年,一直沒有舍得用,只有一次中了毒箭,箭離心臟很近,用了解毒藥劑。”
巫妖掃了一眼那些藥劑,看到上面都貼著標簽,標簽上寫著每一種魔藥的用法和用量,搖了搖頭:“魂體受創,魔法藥水沒有用的。”他又抱歉地微笑了下:“其實我一時也想不起什麼,但是只是直覺……”
蕭偃道:“沒什麼,你從前的情況和現在不一樣,我也拿不準,但是從前你把魂匣讓我隨身戴著,是因為我身上的真龍氣運能夠修復你的魂體,可是現在,你似乎是活人,不知道有沒有用,你先好好休息。”
巫妖其實覺得渾身都疲倦之極,腦子里混亂眩暈,兩耳之間嗡嗡嗡的是巨大的風聲和嗡鳴聲,恨不得立刻閉眼倒下。
但是他現在什麼都想不起來,眼前的人顯然非常難過,他對情緒太過敏感,一直接收到強烈的難過悲哀和沉重抑郁的情感,以及對著自己的期盼、依戀和擔憂。
此人看起來和他自己關系非常親密,他對這幾日隱約有些印象,還記得眼前這黑發黑眼的青年一直在照顧他,喂藥喂水,擦拭身體,他想了下道:“那個紫色的,應該是神圣寧靜藥劑,你拿過來給我喝一點吧,這是精神類藥劑,大概多少有點用。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