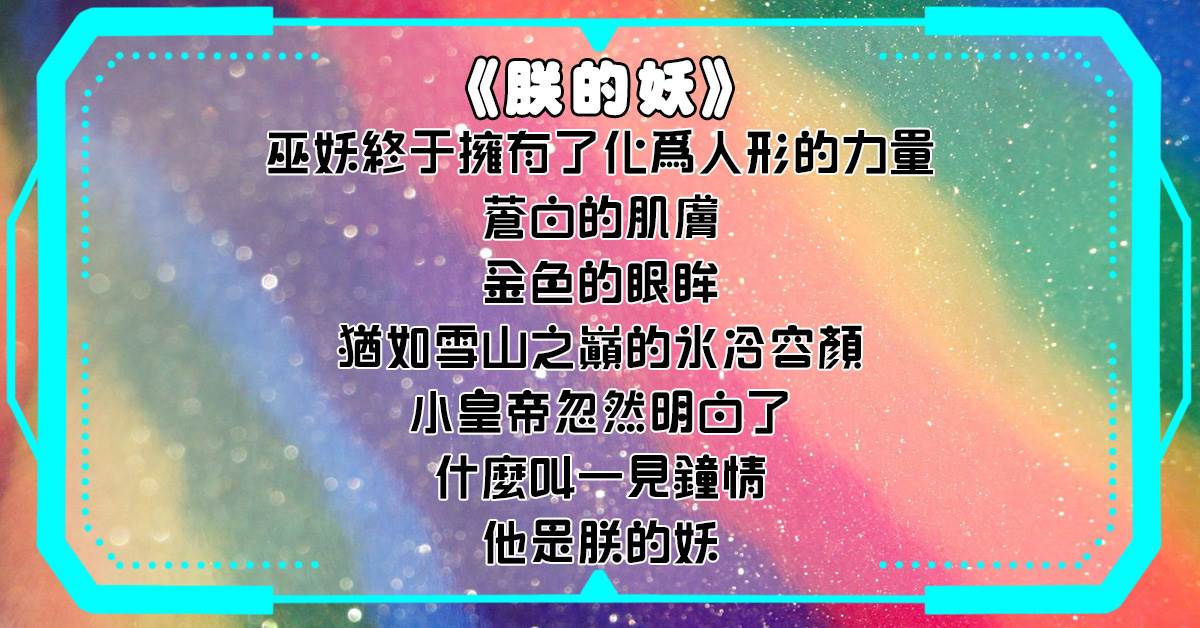《朕的妖》第98章
”
端親王拿著摸了摸,卻又想起一事:“那夜那巫者身材確實頗為高大,我的侍衛大多身材高大,那巫者站在他們身旁,還要再高一些,約莫有八尺余,且渾身披著斗篷,不露相貌,連手上都帶著手套,但進退之時,似看到金色頭發,眼睛也似不是黑色。難道,此人果然不是中原之人?”
歐陽樞文問道:“聲音可有口音。”
端親王道:“倒是十分流利的京城口音。”
三人合計了一會兒,仍不得其法,只能散去。
蕭冀充滿困惑和疲憊的結束了宴飲。第二天一大早,他先參加了朝議,他已久不參加朝議,此次從江南回來,事情也多,他參加朝議倒也不算引人注目。
議事后,他又和兩位相爺談了談皇上如今的教育,騎射課程安排,對季丞相道:“帝王之道,以德為先,法家道理也要講,但以務實為上,但那等神怪妄誕之事,切切不可提之,皇上年幼,不解其中道理,只恐移了性情,前日我和皇上聊事,皇上似對民間巫術有些興趣。”
季丞相看他說得若有所指,微微一愣,回道:“文華閣給皇上授課的大學士,都是飽讀四書五經,多講經義,其二則為古史,倒不曾有人給皇上說這些怪誕鬼神之事。但,英宗當初好道,恐怕宮里有些舊書和舊人會談及這些,我聽服侍的宮人們說,皇上很喜歡自在書房內看書……”
英宗乃是端親王和先帝的生父,季丞相說得已是很客氣了,實際上端親王心里清楚得很,英宗那會兒求神問道已是癡狂的狀態,宮里請了道士修了道觀,日日煉金丹,英宗當時完全不問朝事,到了憫宗朝,憫宗又去世得太早,乃至于其實朝上還真不少歷經三朝的大臣,可都還記得清楚當初英宗是如何荒唐的。
端親王臉色微微青了下,顯然也想起了皇考那幾乎可以說是昏庸無道的求神問道的事來,季丞相又含蓄道:“皇太后又好佛,普覺國師經常出入宮闈,皇上耳濡目染的……”
端親王微微有些暗悔當初心灰意冷,對小皇帝未曾主動教養,皇嫂這些年越走越偏執,也不知道小皇帝一個人在宮里是怎麼過的。
他又問季丞相:“孤此次去江南巡防數月,回來卻聽說高元靈懼罪自殺了?”
季丞相沉默了一會兒道:“內宮中事,我也不太了解其中底細,只知道皇太后不知為何鎖拿了何常安,只說他貪污內庫事宜,內宮事自然皇太后做主,我等也不好過問。但之后高元靈忽然來尋我求助,稱皇太后賜了毒酒給他,我當時只勸他向皇上求恕,沒想到皇上當面叱他驕矜偏執,事君疏慢,納賄營私,賣官鬻爵,不曾恕他。高元靈被斥退后,知道無法,當夜就自盡了。但此事時候回想起來,疑點重重,皇太后要殺高元靈,豈還能讓高元靈有機會出來求救?那毒酒,怕只是有心人挑撥之計,高元靈心虛,中了計。”
端親王心里明白過來,原來小皇帝是從這里破局的,這手段其實簡單,但皇太后多疑,高元靈心虛,倒是正中其兩人軟肋,順利離間。他長嘆一聲道:“高元靈也算惡有惡報。”
季丞相道:“皇太后從前一貫也不是如此冒進莽撞之人,近幾個月頗覺有些糊涂之舉,但究其原因,還是因為非要一意孤行,立承恩侯府嫡女為后。端親王當初若是支持內閣決議……在民間良家女中擇賢作配,正位中宮,也不至于到此,如今承恩侯府聲望愈隆,又攛掇皇太后,在宮里排除異己,宮中這才屢屢生事。
”
端親王卻不想在立后上說什麼,只微微搖了搖頭:“罷了,皇上年歲已長,我聽說內閣已開始請皇上親批奏折,大有進境,這很好,看來今后一兩年,皇上便可躬親大政了。”
季丞相道:“從前總聽皇太后說,皇上體弱多病,圣學未成,奏折未能讀,如何能親政。如今看來皇上聰慧,我已安排文淵閣學士,在當期奏折內挑選適當奏折,為皇上講折。但皇太后又時常問書房功課,訓誡師傅們說功課極多,一時又說以講四書為主,一時又說該當多學實務,又聽說太后在宮內時常給皇上加功課,命皇上抄寫禮記等,如此長久以往,圣學耽誤……”
端親王看了季丞相一眼,淡淡道:“季相,皇太后盛年孀居,對皇上期冀甚大,難免教子有些過于嚴苛,你我為人臣,本就有匡弼政事,輔佐君上之責,自然多規勸為上,總以教導圣上,早日親政為好,國事為重。若是只想著皇上不親政,才好弄權,將這皇上不能親政的責任,推給婦人,那可真有些不厚道了。”
季丞相有些尷尬,笑了聲:“王爺不必太過苛責,皇上如今也才年十二,未為晚也,我看皇上那日面叱高元靈,很有圣明洞見,乾綱獨斷之君威。”
端親王看了下時辰,站起來道:“我去見見皇上。”
蕭偃也正剛剛聽完授課,聽說端親王又來了,想起自己前一日的行為,有些尷尬。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