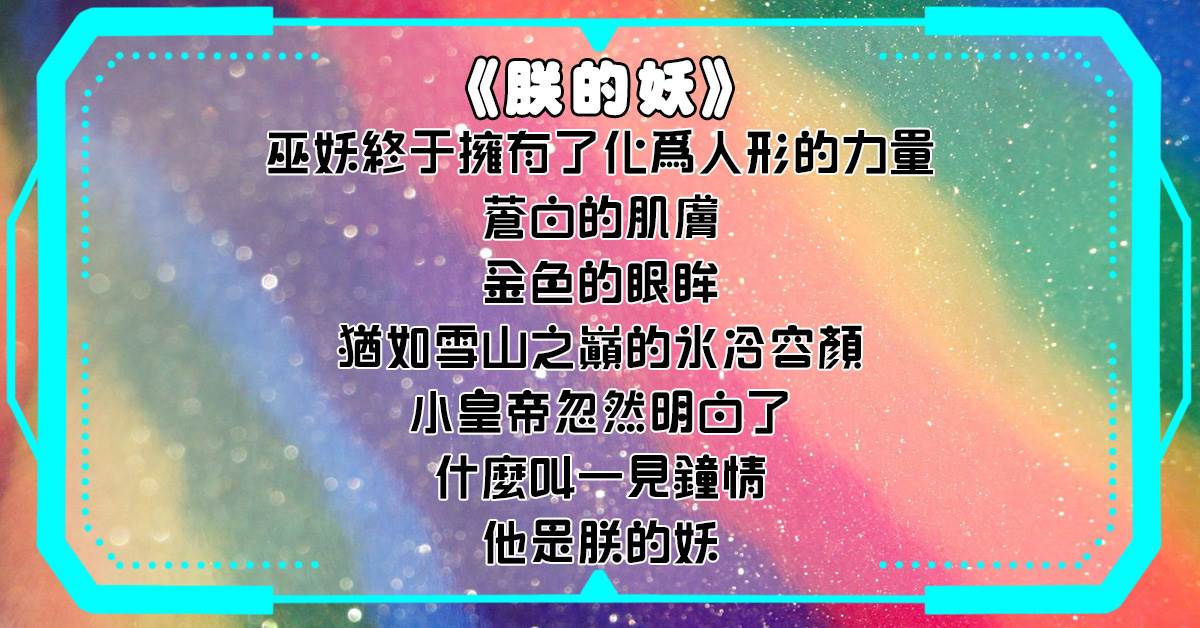《朕的妖》第97章
”
歐陽樞文噗嗤笑了聲:“老國公,您就別戳端王爺心了。”
端親王道:“我這輔政親王,這些年礙了很多人的眼,我若真一病死了,朝廷怕是不少人要放鞭炮飲宴慶賀的。”
安國公道:“倒也不至于,如今北邊不太安寧,好端端自己人先殺起來犯不著,不過圈是可以圈一下,當然要是你自己熬不過那病,那也是天命……”他聲音仿若遺憾,其實滿臉都是笑容。
端親王看了他一眼:“藺江平投敵一事,我知道你們都看不順眼我……”
安國公笑容微斂,面色沉了下去,歐陽樞文卻忙著倒酒岔開話題:“不提舊事,不提舊事,后來呢?那個人,難道真的是大夫?”
端親王卻是從袖中拿了之前那手詔出來,遞給兩人看,一邊道:“不錯,侍衛們上前要逮捕他,卻根本無法逮捕,后來他自稱是巫醫,果真施展幻術,讓我們……都昏迷過去,第二日醒起來后,發現身上的瘟病果然全好了。”
歐陽樞文喃喃道:“一夕之間,便能祛病救人?這是神佛也難做到……是巫?還是鬼?狐?御街從前不就有間宅子,一直說有狐精麼,還會買官帽送住宅的人。”
端親王道:“手段太過詭譎,一言難盡,幻境惑人心智,仿佛真有所見,只能說那絕非正派佛道。孤今日進宮,和皇上說,能否將那名巫醫先安排到孤這邊,讓孤摸摸底細,皇上勃然作色,拂袖而去,看似對那巫者依賴已深,我本以為此名巫者為國公或是駙馬這邊安排,如今看來,如此神鬼手段之人,也不在你們控制中的話,此事更令人心憂了。
此人究竟有何目的?他為皇上做事,皇上又付出了什麼代價?”
安國公卻忽然問道:“宮里高元靈、何常安先后一死一失蹤,端親王可知底里?”
端親王一愣:“內宮事宜,都是皇太后做主。”
安國公卻道:“原本高元靈和何常安等人在,皇太后借他們之手與前朝內閣溝通,結果這兩人先后因細事一個被查,一個自盡,朝野議論紛紛,季同貞倒似稍知內情,但也閉口不言。如今宮里缺了這兩人,皇太后又足疾,因著這些,皇上才開始親批奏折,又得以和你我交通,如今想來,這兩人的死,大有內情,且連皇太后似都蒙在鼓里。”安國公卻沒說,何常安被皇上收在山莊里呢。
這事擺明了是皇上的手筆,但安國公不好說,只能引導端親王自己去思想,好歹爭取端親王這一力量,說起來他確實也太好奇這站在皇上身后的巫者了。
歐陽樞文點了點那張手詔上的朱紅印章:“這上頭蓋的御寶為‘風行草’,我第一次見,風行草偃,皇上志高如是。小皇上心明眼亮,王爺、國公,難道還把他當成孩童嗎?若是皇上心智已昧,被那巫師所蠱惑,當夜就該殺了王爺,而不是反而救王爺,還將這隱藏著的底牌現在王爺眼前,如今王爺若是反要皇上遠離巫者,恐怕皇上也不會聽了。畢竟,高、何二人在時,想來皇上年幼,孤身一人在宮里,日子并不好過,我們有哪個人幫過皇上呢?”
安國公和端親王都沉默了。
良久后,端親王澀然道:“只是你我都知道,這世上人,大多為名為利為權,皇上身系國本。
哪有無緣無故的對人好呢?此人之手段通鬼神,便是你我都駭然,其才干如此,為何要潛伏在皇上身邊?總要知道其緣由,才能放心。”
歐陽樞文也有些自嘲道:“這倒也是,皇太后猜忌于我,將我免職,我也就順其自然,約束大長公主,數年不曾進宮。無欲無求之人,只會將小皇帝視為麻煩,遠離他。”他又看了眼安國公:“老國公也是吧?此前應也只是明哲保身,要不是你家凡君正巧被皇上撞上,你如何會冒險上這條大船?”
安國公呵呵笑了聲:“這明哲保身,有什麼不好意思的,廟堂之高,輪得到你我說什麼做什麼嗎?你看看端王還是輔政親王呢,皇上要立后,他忽剌八跑江南去了,擺明了不想管閑事。咱們誰都別笑誰了。”
歐陽樞文道:“這是小皇上自己走了一條血路出來,殺了高元靈,除了何常安,這才能走到了你我跟前,你我為臣,難道不該效勞君上,為君分憂嗎?”
安國公從袖子里拿出了數枚金幣,放在案上遞給端親王:“此幣為當初皇上給我家那小子,請其采辦用的,我看這紋飾極精美,卻不似中原物事,似是西域流入,這含金的純度也極高,若說到巫者,興許能從這上頭查到來處。”
端親王拿了那幾枚金幣看了下,果然看到有太陽紋的,有花草紋的,都極精美,又遞給歐陽樞文道:“駙馬也看看,可見過?”
歐陽樞文接過來看了下,搖了搖頭:“你看這幣打得極圓整,而且每一枚重量幾乎相等,必是有磨具澆鑄的,一般大族也會自己做些金銀模具,重新鑄些金銀來做慶典或是祭祖之用,但大多不是鑄成金銀元寶方便儲藏,便是做些金葉子銀豆子方便攜帶,做成這樣猶如銅板樣,卻又精心做這樣的花紋,若是名門世族有用這樣的金幣,早就有人知道了,也有私鑄錢幣之嫌,這確實應當不是中原之物,可能是海外或是西域流入的。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