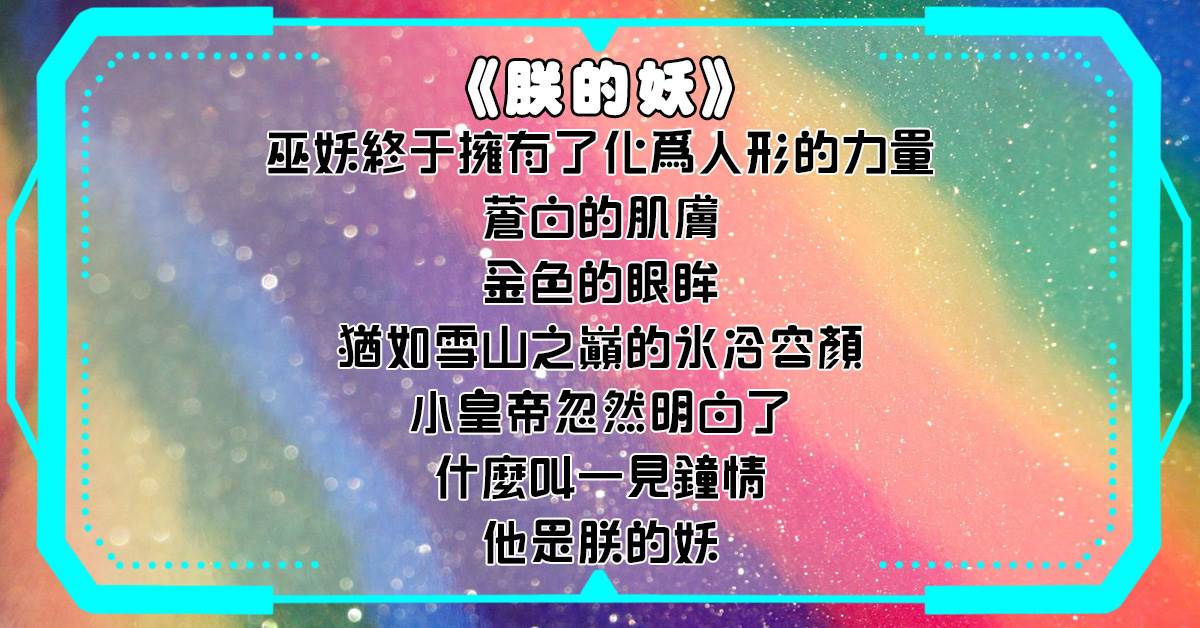《朕的妖》第70章
”
次日,果然蕭偃和從前一般穿著玄色常禮服,在翰林院的明心堂率著翰林院諸院士們,聽大儒講經。
這日講的仍是《禮記》,一章講完,蕭偃退到內殿歇息,才坐下拿起茶杯,只見下邊趨步有內侍過來替他倒茶。
蕭偃抬頭看到一怔:“高公公怎的親自來做這倒茶的活?”
高元靈確實從未替蕭偃倒茶過,此時竟然從小皇帝嘴里聽到了一絲譏諷來,他只能老老實實替蕭偃倒了茶,然后放了茶壺,退下,大禮參拜道:“奴才今日求見皇上,是想要求皇上饒恕奴才的。”說完他又一個頭磕了下去。
他以為說了這句話,小皇上必然吃驚追問。
沒想到蕭偃半日聲息全無,仿佛沒聽到一般。
高元靈額頭抵著冰涼的地板,做出這卑微姿態,只覺得分外難捱和屈辱,心下卻又咬牙想著臥薪藏膽,來日報復的心,只是又等了一會兒,始終不見皇上開口。
他忍不住微微抬頭一看,卻看到蕭偃在上頭,早已放了茶杯,卻是拿了本書斜靠著軟榻在看書。
他心下生出了一股怪異之感,又微微提高了聲音:“奴才求皇上恕罪!”
蕭偃垂眸看著書,滿不在意:“高公公何罪之有?”
高元靈心下忽然一陣悚然,難道,皇上知道太后要殺他?
他顫聲道:“奴才得罪了太后娘娘,太后娘娘如今要殺我,只求皇上看奴才伺候您一場份上,口諭恕罪,奴才今后粉身碎骨,萬死莫辭,報答皇上深恩!”
蕭偃詫異道:“太后要殺你?你犯了何事?如何不經有司審決就要殺你?”
高元靈道:“太后一心想要承恩侯府嫡女為后,奴才卻覺得皇上受制于太后娘娘、受承恩侯府轄制,因此支持內閣諸位相爺的意見,選良家子入宮服侍皇上,此事被太后知道,極不滿,先是無端問罪了何常安,刑訊逼供得了口供,如今何常安生死不知,太后猶不知足,仍要繼續問罪于我,昨日已命人在賜酒中下了毒,奴才命大,僥幸未死。
皇上,求皇上庇護,求皇上口諭,赦免奴才!”
蕭偃玩味地笑了:“這麼說來,高公公倒是對朕忠心一片了。”
高元靈道:“奴才今后為皇上戮力向前,粉身碎骨,絕無半點推托!”
蕭偃又沉默了,大殿內沉悶之極,高元靈感覺到了難言的壓迫感,他的額頭抵著地板,屈辱而詫異地想,昔日那單薄又唯唯諾諾的小皇帝,什麼時候竟然這麼有威嚴?
蕭偃終于發話了:“高公公,還記得韋翠娘嗎?”
高元靈忽然汗濕重衣:“皇上饒命!當時奴才一切都聽太后娘娘的,并非故意!”
蕭偃嘴角微微帶了些冷笑:“朕從藩地進京入宮,當時年幼,到了陌生地方,全賴乳母照顧和安撫。高公公你以韋氏離間朕和母后感情為由,當著朕的面,將韋氏活活杖死了。”
高元靈手都在微微發抖,皇上竟然一個仇記了這麼些年!當時他才幾歲?
蕭偃淡淡道:“你故意當著五歲的朕的面杖殺乳母,不就是想讓朕對你言聽計從,畏懼你嗎?”
“”如今,你要讓朕赦你?”
高元靈深深將額頭觸在地板上,這句話讓他心里充滿了絕望。
“你深受皇太后及朕深恩,在司禮監多年,驕矜偏執,事君疏慢,朋比作奸,貪婪不法,納賄營私,賣官鬻爵,貪劣實跡斑斑,實乃怙惡不悛之人。”
“若不是看在皇太后面子上,朕早已處置了你,你居然還敢到朕跟前,求朕赦免,給你一條活路?”
高元靈咬了咬牙,不再解釋舊事,只是又忽然高聲道:“皇上,奴才該死!但奴才這條賤命無妨,皇上想什麼時候拿走都可,只是皇上如今需要人手,奴才愿為皇上效勞!奴才愿做皇上的狗,皇上讓我咬誰就咬誰!奴才愿做皇上的刀,皇上想殺誰,奴才決不臟了皇上的手!只求皇上留奴才一條賤命,奴才手里還有內閣諸相,邊疆大將,朝廷勛貴重臣的許多陰私不法事,奴才可交給皇上,此后他們都會聽皇上的,為皇上效勞!”
高元靈底牌盡出,抬起臉來,臉上帶了些癲狂亢奮,他不信小皇帝還不動心!只要給他翻身,只要給他機會翻了身!
他上前痛哭流涕,將額頭咚咚磕在地上,血飛濺了出來:“皇上!奴才薄有資產,所有家財鋪子,可盡充皇上內庫,又有訓練好的死士三十人,擅偵聽機要,緝捕暗殺,人人皆可為皇上效死!”
堂上仍然安靜極了,蕭偃輕輕笑了聲:“原來高公公是用這樣的手段挾制朝堂大臣們的,朕也算開了眼了。”
高元靈嗚咽道:“今后奴才就是皇上的一條惡狗了!”
蕭偃輕啐了聲:“你配嗎?”
他站了起來,緩緩道:“朕為君,豈能用爾等小人之手段治國御下?你也太看不起朕了。”
高元靈癱軟在地下,蕭偃淡淡看了他一眼,拂袖走了出去。
才出門轉過走道,蕭偃便看到了季同貞,季同貞深深俯首躬身行禮。
蕭偃看了眼他,淡淡道:“昔日高太傅舉薦季卿為相,是因為卿家公忠體國,辦事勤敏,賢明才高,只希望季相您好自為之,”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