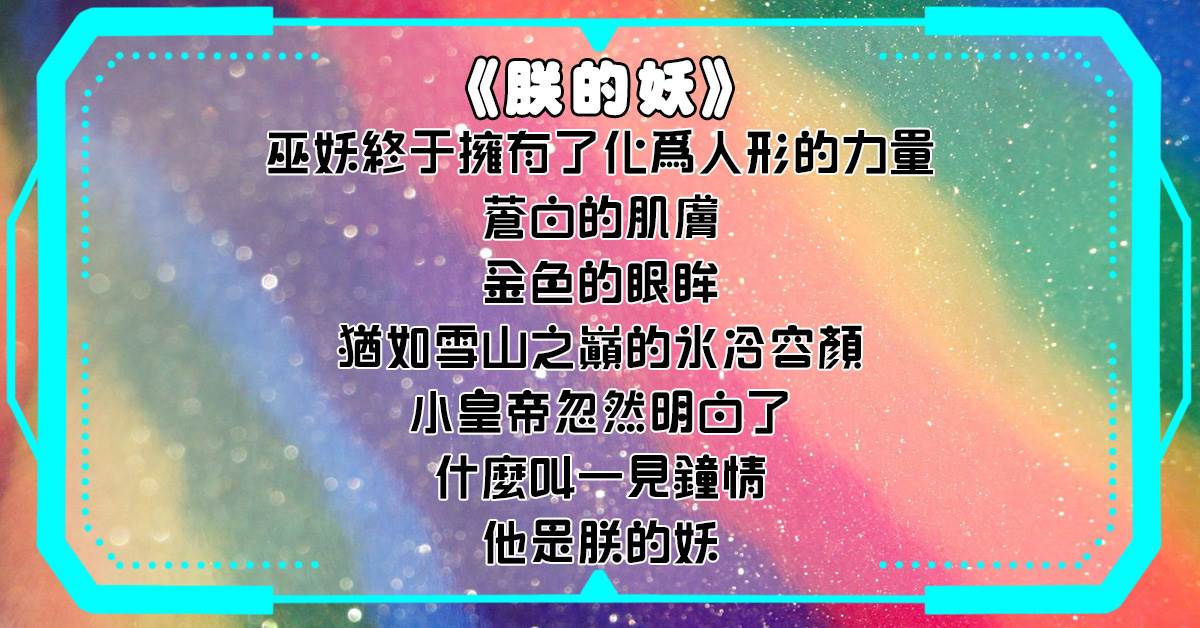《朕的妖》第69章
”
孫太后道:“他必還會找內閣左右相,此事不能掉以輕心了,有何常安的事在前,高元靈以為是被哀家賜毒酒,必定要想法子針對哀家,哀家寫一封信,你即刻出宮,親自交給承恩侯,并且將今日的事原本講給承恩侯聽,問他有何辦法,哀家猜,他們定然要從皇上親政下手了。”
吳知書點了點頭:“奴才謹遵太后娘娘令。”
孫太后又想了想,笑了聲:“不過,倒也不必太著急,他想還政于皇上,內閣兩位相爺怎麼舍得?他們背后還有延綿不絕的同鄉、同科、同年呢,如何舍得這麼早就還政?就為了一個喪家犬?只可惜,高元靈這枚棋子要廢了……司禮監卻不能就這麼放棄。”
她有些不滿看了眼吳知書:“你太不濟事,否則早就讓你頂上了,如今倉促之間,去哪里找個知根知底的人頂上。”
吳知書只能深深低下頭去,孫太后道:“把司禮監當值的幾個秉筆太監都叫過來,哀家問話。”
吳知書知道孫太后這是打算從副手中暫時提人上來了,心下不由一陣心痛大好的機會,可惜……自己卻是才疏學淺,那幾位秉筆太監,可的確是熟讀經書,學問甚好,還時時得大學士們教導的,他如今也只能殷勤應了。
孫太后自己一個人寫了一封信,用蠟逐層封箋蓋印,封了密密幾層,交給吳知書,這才閉了眼睛想著自己的謀算。她身后,龔姑姑悄步走了出來,低聲問:“之前說大姑娘那事……”
孫太后揉了揉太陽穴:“暫且先放一放,如今高元靈生變,這背后施此計的人更是毒辣,將高元靈硬生生從哀家的助力推到了對面,端王又不在,哀家孤掌難鳴,沒得助力。
閣臣們本來就忌憚哀家,高元靈再搗鬼,這宮里還有別人在搗鬼,還有安國公……哀家要好好應對這事,她在深閨中,又是待嫁,規矩森嚴,左右也不會亂走亂說,有哥哥管束著,不急。萬一處置不好出了差錯,倒是給對手遞刀子送把柄,且先放一放。”
孫太后又想了想道:“讓尚宮局賜兩個老成些的女官到承恩侯府,就說教她規矩,看好她了,莫要讓她閑下來。”
龔姑姑低聲道:“是。”
左相季府。
季同貞青衣紗帽,坐在太師椅上拿著茶杯,簡樸如個普通讀書人一般。他慢慢喝了口茶,眉心微皺,看著面前形容狼狽的高元靈:“太后怎會無緣無故鴆殺你?”
他又仔細看了看高元靈的臉色:“吾略通醫術,看您也不似才中毒的樣子,面色紅潤,雙目有神,神完氣足,若是劇毒,便是僥幸不死,豈能讓你還能行走言語如常?”
高元靈聲音嘶啞:“季相,無論是不是,嫌隙已生,我是服下太后端午賜酒后腹痛,多人看到,宮里人多嘴雜,太后會相信我不疑她嗎?譬如當日高祖賜鵝于發背瘡的重臣,無論是不是,都只能死,我不過是個奴才罷了,太后要賜死我,不過一句話罷了。”
“有何常安在前,太后此舉無論是不是警告,我都只有死這一條路了。”
“我在司禮監數年,為相爺辦事也不少了,如今太后動我,顯然是覺得我偏向內閣,不合她的心意了,她如今隱忍,不過是為了皇上大婚,一旦承恩侯府嫡女進宮,宮里又多了一位皇后,屆時,我們行事只會更艱難了。
”
高元靈說得懇切,看了眼季同貞一直沉吟不語,又微微面露威脅:“相爺難道覺得,我手里就真沒有些自保之力?只是想著和相爺多年情分,不至于走到玉石俱焚之境地,相爺和諸位老大人,都是金玉,家族興旺。莫非也要和我這等孤身一人無兒無女的奴才一起共沉淪嗎?”
季同貞微微笑了下:“高公公,老夫辦事,那都是為國為民,便是有些不合規矩之處,那也是為了大局,可不是滿足私利,便是到皇上跟前,老夫也是俯仰無愧的。公公也莫要著急,此事不至于到絕處,我給公公指一條明路,為今之計,只有一人能救公公了。”
高元靈一怔,季同貞慢慢向上拱手道:“為今之計,只有皇上能救你了。”
高元靈原本驚異,隨后卻又深思:“公公的意思是?”
季同貞道:“皇上龍潛于淵,少年聰慧,前些日子你也看到了,安國公三朝元老,力挺皇上親政。皇上,已經隱隱能與太后分庭抗禮,高公公不如坦誠相告,求皇上赦之,則既有皇上口諭,我們內閣自然遵旨,太后便無法再對你做什麼了。”
季同貞慢慢道:“皇上勢單力薄,宮里若得了公公助力,親政之日指日可待。因此,若是公公心誠,皇上定會赦你保你。”
高元靈心頭豁然開朗,深深一躬拱手道:“季相指點之恩不敢忘,但有一事尚需相爺相助,如今我一進宮只怕就要生變,還需要季相相助面圣才可。”
季同貞從容道:“此事簡單,皇上明日到翰林院聽經筵,我安排你面圣即可。”
高元靈一聽果然正是講經的日子,太后手未必能安插到翰林院,心下微定:“元靈這條小命,就全仰仗相爺了。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