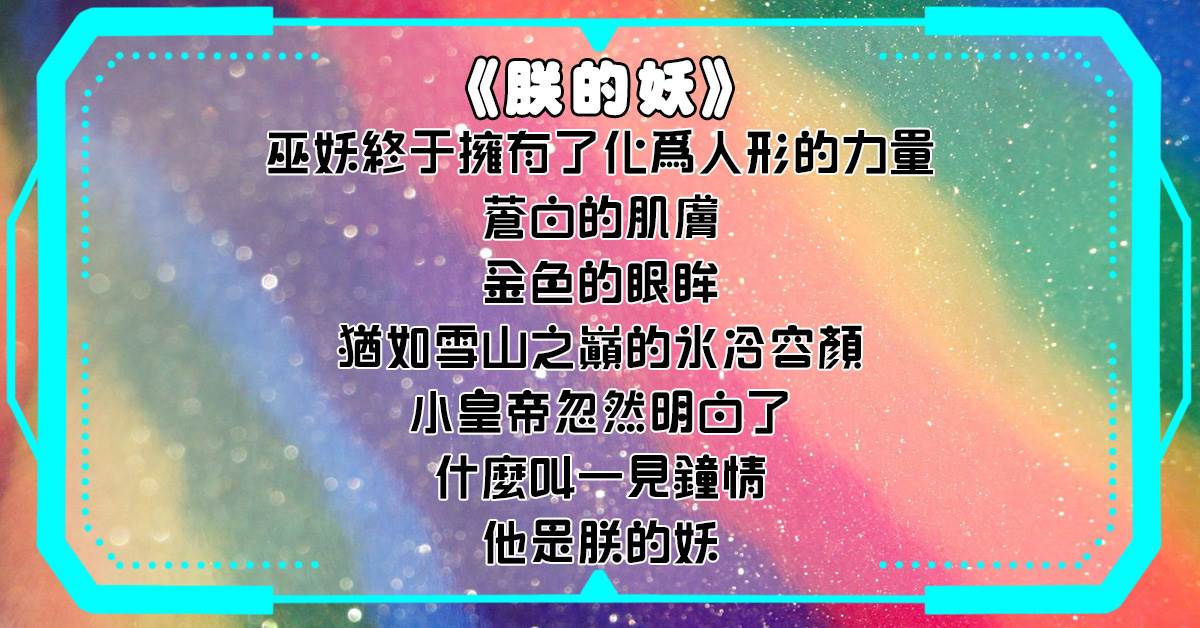《朕的妖》第27章
融掉再用倒是使得,但是,這麼精美的錢幣,他舍不得融,另外小皇帝在深宮里,進出圍著無數從人,小皇帝是怎麼從守衛森嚴的禁宮里微服出來無人知曉的?又是如何拿出這樣明顯是有世家專門鑄造的精美金幣來購房?小皇帝身后到底是什麼勢力再幫他?能幫他出宮,能給他這麼多金幣,卻沒辦法替他購置房舍嗎?
是遠在津州的皇帝的親生父親,津王嗎?
津王一直被太后牢牢打壓著,難道還是在京里有了自己的勢力?
所以,皇上是在試探自己嗎?全怪自己一腳踏進了那包間!
衛凡君簡直郁悶得要吐血,卻忽然被蔣建良推了下,他一怔,回過神來,卻看滿堂的人都看著自己,就連上首坐著的蕭偃都看向了他,眸光平淡。
丁嘉楠學士又問了他一句:“衛小公子,你今日交的文論,你來說一下。”
今日交的文論?那是讓安國公府的清客代寫的,平日上學前他都會看一看背一背,以免露餡,但昨晚他一夜未寤,哪里還顧得上這作業?
衛凡君滿臉漲紅,支支吾吾,說不出話來。
丁學士有些生氣,稟蕭偃道:“怠惰學業,不敬師長!還請陛下同意,傳戒尺。”
學宮里的懲罰,一般都是教授定奪,但天子尊崇,因此一般講授的值講大學士們,都會先稟蕭偃,征得同意后方傳戒尺,由宮里負責懲戒的內侍們代為執尺行罰,而若是陛下有失,則全體伴讀一概受罰。
蕭偃一貫也尊師重道,從無不許過。
衛凡君臉色紅紅白白,蕭偃看了眼衛凡君,徐徐和丁學士道:“朕看凡君今日面容憔悴,似有疾病,不若權且寄下,待他就醫身子康健后,再罰不遲。
”
丁學士有些訝異,但一眼看衛凡君確實面色青黃,倒也沒必要為了這點小事逆了君上,便也道:“陛下寬慈,那就權且寄下,下一旬考,若是考不到良,一并罰了!”
衛凡君面色恍惚,跪下應了聲,抬眼看了蕭偃早已拿了書起來,不再關注他,只能訕訕在眾人的目光里回位,渾渾噩噩混到了今日課結,跪下恭送蕭偃離開,臨走前他偷偷看了眼蕭偃,淡色的唇和冰冷淡漠的側臉,仍然一如既往的冷漠寡言。
皇上頭一次為伴讀說話,這讓伴讀們也十分意外,送走了值講的大學士和皇上后,衛凡君很快被其他伴讀揶揄:“衛兄什麼時候入了皇上的眼,竟然能被皇上為你說話?”
衛凡君滿口苦澀,臉上肌肉硬結:“陛下一貫仁厚……我聽說,陛下還把祁垣也要到了身邊伺候照應著。”
說到祁垣,眾人都靜了靜,似乎都不知道如何評論這個前任的同學,如今宮里最卑賤的奴仆,卻又陪伴在小皇帝身旁。
在座的伴讀們都出身權貴,此時不免有些唇亡齒寒之感,人群里有人冷笑了聲:“這樣的帝寵君恩,安知是雷霆還是雨露呢?”
卻是理國公之子柳曉儉,他一貫功課上十分刻苦,卻偏偏天資一般,平日里也只是表現平平,因此看衛凡君如此紈绔卻反而得了皇上解圍,不免有些酸溜溜。有人立刻將他衣袖拉了一下,眾人只怕惹事,匆匆都走了。
衛凡君在座位上呆著了一會兒勉強收了筆墨,蔣建良寬慰他道:“他們是嫉妒你,皇上替你解圍,這是好事。
”
衛凡君心里卻想著,所有人都知道皇上身不由己,乃是個大大的傀儡,到底是誰在幫皇上呢?
他沒說什麼只出了宮,回家卻是找了個靠譜的老仆來,密密交代了一回,又從自己手里拿了些銀錢,老仆接了銀錢,二話沒說按小主子的說法出去辦事去了。
而慈福宮孫太后那邊自然也接到了皇上這日為衛小公爺說話的稟報,她笑了問:“那衛凡君,是安國公府的吧?哀家記得,長得特別好,就是學識上不大長進,只是安國公早早沒了兒子,對這個孫兒那是千方百計地寵,當時哀家挑了他來做皇上伴讀,安國公親自來求我,說他家孩子年幼,在家寵溺慣了,又很是駑鈍,希望哀家照拂,哀家當時答應他宮里多照應著。”
學宮里乃是秉筆太監高元靈管著的,此時笑到:“太后娘娘照應自然是應當的,只是奴才只擔心陛下年少,今日開口護著這個,明日開口護著那個,長此以往,伴讀們讀書便也不精心了,到時候帶得皇上也疏怠了功課。就怕傳出去,御史們多嘴,又要參皇上。”
孫太后笑了下:“高公公說得極是,只是如今只是第一回 ,若是哀家這就駁了他,皇上面上須不好看,畢竟他也大了……譬如前日那祁垣……”
孫太后想起來又問身邊人道:“那祁垣如今在皇上身邊當什麼差?”
一旁小道:“回太后,仍是抄佛經呢,可巧今日才送了三本全的過來,一本《地藏經》、《陰鷲經》、《法華經》,奴才看過了,果然字又大,又舒展好看,容易讀,紙張用的也極好,可見是用心辦了差的。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