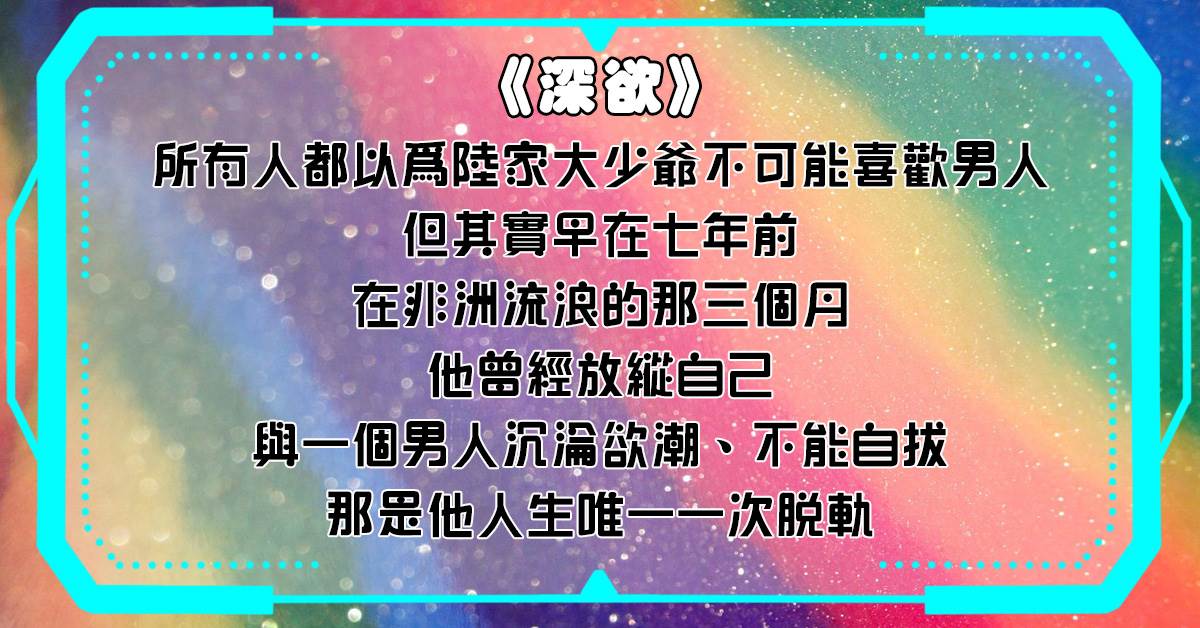《深欲》第93章
陸璟清握緊咖啡杯,神色中出現了些許掙扎,眼里的戒備卻逐漸放下了:“……你對阿深是認真的嗎?如果只是隨便玩玩,就別再招惹他,無論他有沒有問題,都跟你無關。”
“我想知道,”封肆堅持,盯著陸璟清的眼睛,“煩請告知。”
他的語氣并不強硬,陸璟清卻莫名感受到了壓迫感,這讓她十分不快,但想到陸璟深這段時間以來的失魂落魄,似乎一切又在重復七年前他從非洲回來后的狀態,那時她單純以為是陸璟深的心理問題所致,到今天才忽然意識到,癥結或許還有面前這個男人。
“我之前也不知道他會喜歡男人,”陸璟清終于松開了防線,“他確實恐同,心理上有很大問題。”
封肆:“為什麼?”
陸璟清的眼里有轉瞬即逝的晦暗:“PTSD.”
封肆的眸色動了動,陸璟清快速說下去:“我跟他都是在美國念的大學,在不同的州,你應該很清楚,同性戀在這個時代雖然很常見,西方人嘴里也一直念叨著政治正確那一套,但保守的地方一樣很保守,尤其在美國,不同的地域間觀念相差巨大,阿深念書的地方,就是偏保守那一派的,他的同學很多都信教,對同性戀持反對態度,但也有例外。”
“其中有一個男生偷偷跟校外的男人談戀愛,后來被傳染了艾滋被拋棄,又被人在學校里惡意曝光私生活,從那以后所有人都繞著他走,連小組作業都沒人愿意跟他一組,大概是看阿深好說話,教授安排那個男生跟阿深一起,阿深那時對同性戀的態度是事不關己,性格使然,他更不會像其他人一樣把歧視擺在臉上,一直就用對待普通同學的態度如常對待那個男生,就因為這樣,那個男生卻把阿深當成了救命的稻草。
”
“他趁著阿深獨自出門買東西時,用電擊棒擊暈了阿深,綁架了他,將阿深鎖在不見光的地下室里,一遍一遍地向阿深訴苦,訴說他跟那個男人的愛情,憎恨那個男人把病傳染給他又拋棄他,想要阿深理解他同情他,他那時已經病入膏肓,染上艾滋后在很短的時間內發病,加上嗑藥,身體已經垮了,精神也不正常,但是阿深沒有給出他滿意的反應,只想離開,所以他發了瘋,給阿深注射致幻劑,將阿深獨自關在地下室里,通過監控拍下阿深被注射藥物后丑態畢出的視頻和照片。”
陸璟清說得很快,這件事情對她來說,也是不愿意再回想的記憶。封肆眼里的情緒一點一點沉下,轉換成了另一種十分復雜的,難以用言語形容的沉黯:“后來呢?”
“后來,”陸璟清像不忍心說下去,“后來,阿深被救出來,已經是兩個星期以后,那個男生嗑藥過度死在了出租屋里,還是隔壁的住戶發現他的尸體報了警,警察去了才發現被關在地下室里,已經奄奄一息的阿深,那個時候他已經快三天沒吃過東西,僅靠半瓶礦泉水強撐了下來。”
“被人救出來時,他看到了那個男生腐爛發臭的尸體,當場就吐了,因為太久沒有吃過東西,吐出的只有胃酸還嘔了血,我收到消息趕過去時他已經進了醫院,住了大半個月,身體是痊愈了,心理上卻留下了嚴重后遺癥,有一段時間他甚至整夜失眠、做噩夢,產生幻覺,差一點連學業都沒法繼續。
”
“這件事情只有我跟他知道,他不想讓爸媽擔心,一再要求我不要跟家里說,我幫他瞞了下來,出院之后還幫他請了心理醫生,他去看過幾次,因為過于恐懼和排斥,幾乎沒什麼效果,后來他不肯再去,畢業后他說想一個人出去散心,我其實不放心,打算跟他一起,他沒肯,堅持一個人走了。”
“后來我才知道他去了非洲,有一天他突然給我發消息,說暫時不打算回來,會在那邊待幾個月,這段時間都不會聯系我,讓我別擔心他,之后就關了手機,我一直聯系不上他,憂心了整整三個月,他才回來。”
“那之后他就像變了個人一樣,以前就不愛說話,從那以后變得更封閉自我,我還是想讓他去看心理醫生,他說不用,后來我們回國開始進公司工作,我看他表面上似乎恢復正常了,也覺得沒有必要再讓他去面對那些傷痛,就再沒跟他提過這事。”
陸璟清神情復雜地說完,眼睛直視向封肆:“你聽懂了嗎?我不想逼他,所以希望你也別逼他,他做的不好,不管是當年還是現在,你要是接受不了就算了,沒必要非逼著他放下對同性戀的恐懼,經歷過那種事情,我想是個人都很難做到。”
“你真的覺得他恢復正常了?”封肆冷靜問她,“他現在的問題,你覺得僅僅是對同性戀恐懼,對自己同性戀身份的不認同?你沒有發現他連正常的社交都成問題嗎?”
陸璟清立刻反駁:“不可能,這些年他無論是面對家里人,還是工作上,都沒出過什麼差池,能有什麼問題?”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