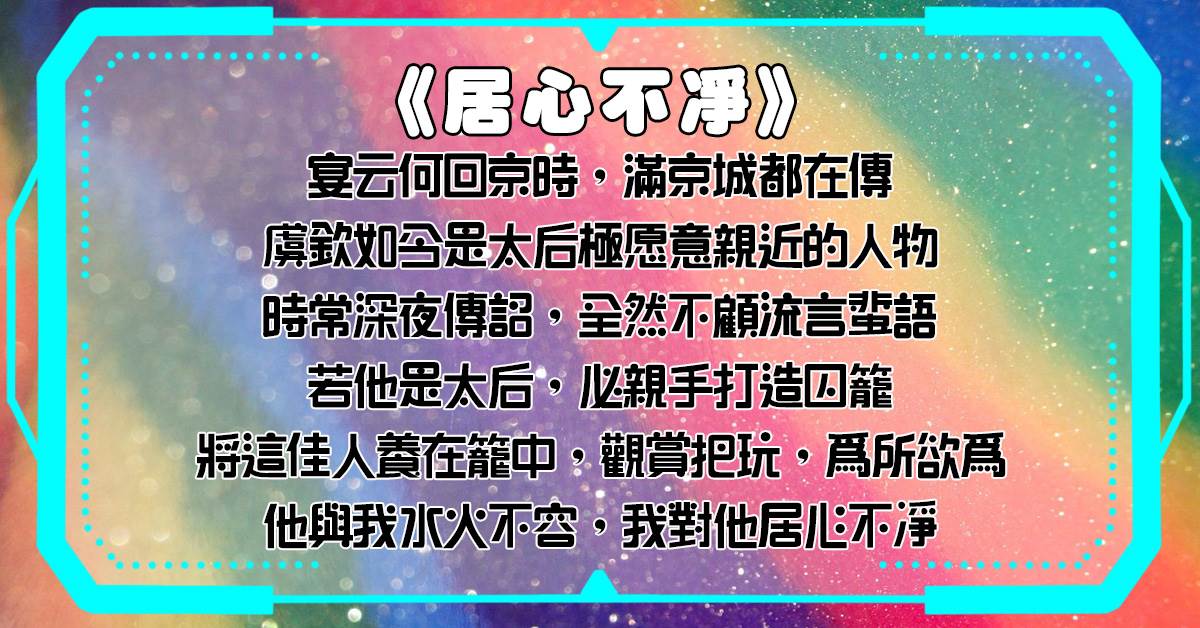《居心不凈》第170章
”
虞欽冷靜到近乎殘酷,他早已想得清楚,也知一年后的京城,不過是在荊棘上鋪滿錦繡,比身負污名的死去好上些許。
宴云何徒勞道:“或許沒你想象的那麼糟,等時間久了,姜黨無人提起之時,你展現自己的能力,怎會得不到重用。”
虞欽搖了搖頭:“淮陽,現在已經比原本想的好太多了,我很滿足。所以殺簡九可能是我能幫你做的最后一件事,也可能是為這江山社稷盡的最后一份心。不管今后如何,我只求問心無愧。”
宴云何望著虞欽許久,眼眶逐漸泛紅:“寒初還真是……”從來只對他心狠。
言盡于此,宴云何又怎能繼續阻止。
他自然明白虞欽現在的感受,復仇后的感覺不是大功告成,再無遺憾。
而是需要面對自己因為仇恨而犧牲的一切,再回首瞧那滿目瘡痍。
哪怕因為仇恨滿手鮮血,可他沒忘記自己最開始的模樣。
同樣,宴云何也從未忘記過。
虞欽瞧見宴云何竟然被他逼成這樣,慌忙道:“這些日子在藥王谷待著,好些舊疾都治好了,我身體沒你想象中的那麼糟糕。再不濟些,刺殺不成也能逃離,我答應你絕不戀戰。”
宴云何閉眼壓去眼中淚意,人一但有了軟肋,便會瞻前顧后,變得軟弱。
哪怕知道這是最優選擇,也不愿做。
睜開眼時,宴云何已經下定決心:“你可以去,但是若到了時間你還不出來,我會立即發起強攻。”
虞欽知道他是終于同意的意思,宴云何又囑咐道:“你要多帶上幾個幫手,聽令行事,不可擅動。
”
直到聽人說了聲好,宴云何不再多言,而是疲憊地躺了下來,經這一遭,竟然覺得比打仗還累,心口也是沉甸甸的,似有重物壓得喘不上氣來。
虞欽跟著一同上床,摟住宴云何的腰身:“淮陽。”
他什麼也不說,只是輕喊著宴云何的名字,小心翼翼地好像一場試探。
宴云何沒有回應,也不動彈,就似躺下后已然入睡。
但虞欽沒有就此放棄,而是收緊了摟住他腰的力道:“同我說說話。”
宴云何仍然不動,虞欽取下面具:“淮陽,我臉上有些疼,你幫我看看可好?”
話音剛落,就見宴云何眼睫微顫,但始終沒有睜開。
他從來是慣著虞欽的那個,對于很多事情也是步步退讓,這不代表他沒有脾氣。
只是舍不得,放不下,離不了。
如果可以,他恨不得時時能盯著虞欽,刻刻護他周全。
但他所愛之人,不是池魚,非籠中鳥,他困不住,也不想困住。
耳垂一痛,是虞欽叼住那處磨了磨,像是報復臉上的牙印般:“你先前說我不該瞞你,現在征求你同意,怎麼還是生氣?”
宴云何驀然睜開眼,直直盯著虞欽:“那是一回事嗎?”
虞欽見他終于睜眼,突兀伸手掐住他的臉頰,強硬地將他轉到自己方向,吻住了他的嘴唇。
宴云何無心親熱,掙扎地想從虞欽唇舌間逃離,卻被用力吮住舌尖,力氣大得宴云何都感覺輕微發麻。
唇齒相纏的水聲,一時間變得極響,粗重的呼吸也在營帳中愈發清晰。
宴云何感覺到虞欽掐住他腰的力道變得有些重,指腹在他側腰上大力揉捏,帶著一種不尋常的焦躁。
很快虞欽克制地停下親吻,拉開兩人距離時,目光不離宴云何喘息的雙唇。
宴云何正在平復氣息,就感覺到虞欽將手壓在他的嘴唇上,不止是觸碰,而是越過禁忌,探入那濕潤綿軟的內側,直至碰到柔軟的舌尖。
這讓宴云何合不上嘴,眼尾仍帶著方才沒有褪去的濕意。
近乎縱容地仍有虞欽的指尖,在他嘴里肆意地觸碰。
未能咽下的唾液順著嘴角淌,宴云何終于皺眉合上齒關,咬住了虞欽的手指,目光譴責對方,不要太過放肆。
虞欽這才回過神來,將手從宴云何的嘴里抽出:“好像把你舌尖咬破了,伸出來讓我看看。”
宴云何這回卻不配合:“沒有破。”
虞欽有些可惜地看著他的嘴唇:“真的沒有嗎?”
宴云何嗯了聲:“你要是在這次刺殺行動里受了重傷,等你回來,我會把你綁在床上,讓你試試看我的舌頭到底有沒有破。”
說完,他目光意有所指地移到了虞欽臍下三寸。
虞欽臉立即就紅了,也不知道想到了什麼:“胡鬧。”
宴云何面無表情地說:“要不是我現在身上有傷,我會讓你知道什麼叫真正的胡鬧。”
“隱娘說這營帳里透光,你猜猜看門口的親兵知不知道我們在做什麼?”宴云何故意道。
虞欽身子一僵,似乎不習慣宴云何這突然的直白。
他坐起身,轉移話題道:“你是不是該同部下們商討刺殺以后,無論成敗都該有的應對之策了。”
“的確該叫人過來議事了,在此之前,我想問一句…… ”他頗為認真道:“這就是你哄人的法子嗎?”
虞欽尷尬地望向宴云何:“怎麼了?”
宴云何心里默念清心咒,好將那些邪念壓下去,低聲道:“沒什麼。”
等一切結束后,他要將虞欽五花大綁,想怎麼弄,就怎麼弄!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