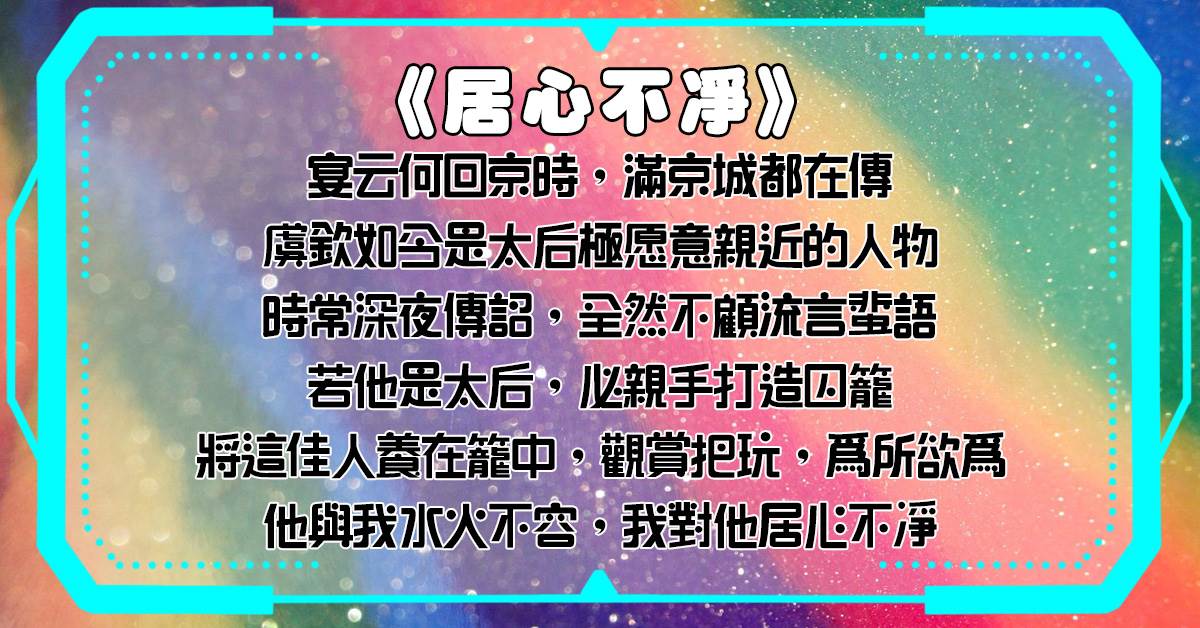《居心不凈》第127章
后來因為喝酒一事,宴云何又被永安侯狠狠罰了一場。
那夜同虞欽的親吻,逐漸變得像夢一場。
他回到東林以后,虞欽仍像從前那般冷淡,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如果宴云何真的趁醉冒犯了虞欽,他想以虞欽的性子,待他回到東林,不殺了他才怪。
正因虞欽沒有任何反應,反倒叫宴云何認定了那不過是場夢。
現在宴云何才知道,這非但不是一場夢,而虞欽原來早在十年前,便知道他心儀于他?!
他們的第一次親吻,竟這樣早就發生了?!
宴云何震驚又錯愕:“虞欽,你怎麼這般能忍,我都趁醉親了你,你竟然能裝作什麼事都沒發生過,還瞞我瞞了這樣久!”
虞欽見他模樣,便知道這人已經將當年的事情盡數想起:“是你將它當作一場夢,我不過是配合你罷了。”
宴云何回過神來,漸漸覺出不對:“寒初,你瞞著這事,可是因那時便已對我動心?”
虞欽卻道:“什麼心,殺心嗎?”
宴云何噎住了,這麼想想也是,那時覬覦虞欽的這麼多,還沒誰像他那樣膽大包天,動手動腳。
雖是自己做錯了,但虞欽怎的這麼老實,連哄哄他也不愿意,他垂頭喪氣道:“我錯了。”
這一場遲到十年的酒后算賬,卻從今夜才開始清算。
虞欽問他:“何錯之有?”
宴云何老實道:“不該酒后輕薄于你。”
虞欽頷首,那模樣瞧著與當年教訓宴云何的夫子,一般無二:“日后不許過多飲酒。”
宴云何忙抬頭:“可是出門應酬,難免有飲酒的時候。我并非不想答應你,只是答應以后若是做不到,豈不叫你失望?”
“所以我只是讓你不要貪杯,沒叫你不許飲酒。
”虞欽說道。
宴云何剛挺直的腰板,又緩緩彎了下去:“好,日后不會了。”
虞欽見他模樣低落,嘆了口氣:“我觀你身上舊傷累累,飲酒對此有害無益。”
宴云何聽著這話,心頭又滿漲起來,他慣來好哄,剛想笑著說點什麼,便聽虞欽道:“從前你是酒后尋我,若是日后尋旁的人呢?”
“怎會!”宴云何瞪大眼:“你不能污蔑我,我定是都找了你,沒有別人!”
虞欽挑起眉梢:“你在邊境那些年,可有醉過。”
宴云何立即道:“就是醉了,也有成安在旁照料,沒聽他說過我有酒后亂跑的事。”
聽到這里,虞欽眉眼微動:“趙成安?”
“嗯,成安是我最好的兄弟,性子也好,模樣也俊,在我們營里很受歡迎,多的是人想把自家女眷許配給他。”宴云何興高采烈道。
哪知虞欽竟聽著聽著,神情淡了下來:“看來你覺得他很好。”
宴云何的神經前所未有地繃緊了,他敏銳地嗅到了不對,當即說道:“嗯……其實也沒那麼好,我與他就是脾性相投。”
“還互為知己。”虞欽不緊不慢地補充了后半句。
宴云何快被冤死了,總覺得今晚不管說什麼都是錯的。
他忙擺手道:“也不能說是知己,不到那種程度。”
“說笑罷了,你怎麼如此認真。”虞欽口風一轉,很是淡然道。
可憐宴云何在這冬夜,連額上的汗水都給逼出來了,他小心地瞧著虞欽:“你當真沒有生氣?”
說實話,虞欽在宴云何眼中,自然是千好萬好的。
但宴云何也沒被愛意蒙蔽了雙眼,當初便知道這是個心狠美人,即便如此,但他就愛他這模樣。
也愛他氣性大,為他吃味的樣子。
“若是事事都要生氣,那在下真要未老先衰了。”虞欽道。
宴云何想到他招惹虞欽這麼多回,的確時時叫人生氣,說的那些話也很不好聽。
尤其是回京以后,虞欽都被他刺得同他動了幾回手了,想想就背脊發麻。
宴云何立刻討饒道:“寒初就大人不記小人過,饒了我從前不懂事。日后你指東我絕不往西,事事都聽你的。”
“此話當真?”虞欽問道。
宴云何頓了半晌,才換了措辭:“嗯,如果你說的有道理,我就聽你的。”
虞欽終是露出了今晚的第一次笑,宴云何的心也隨著他的笑容,軟得一塌糊涂。
若是能時時叫虞欽開懷,那他做什麼都可以。
虞欽很快便斂了笑意:“我該回去了,你好好歇息,若是有事,記得城南桃花。”
宴云何頗有些依依不舍,他望著虞欽:“過兩日便要開始準備冬狩,到時候忙起來,或許就不能像如此這般日日相見了。”
虞欽聞言,卻還是起身來到門邊。宴云何隨在他身后,送他出去。
哪知虞欽走到門邊,卻又停下腳步:“要是我留宿侯府,被旁人察覺,于你是否有礙?”
宴云何被這突如其來的驚喜,砸得不知如何是好,忙道:“怎麼會,你要是肯留下來,我會安排好一切,不妨事得。”
虞欽將門緩緩合上:“那今夜便麻煩淮陽了。”
宋文本就隨時在外候命,已經有些發困。
宴云何突然吩咐要用水,他還揉著眼睛道:“大人,你不是早就梳洗過了嗎?”
說完他突然臉就紅了,結巴道:“大、大人,你怎麼如此大膽!”
宴云何對準他的額心,彈了一記。
他手勁大,彈得宋文腦瓜子嗡嗡作響。
宋文捂著額頭:“大人,很痛啊。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