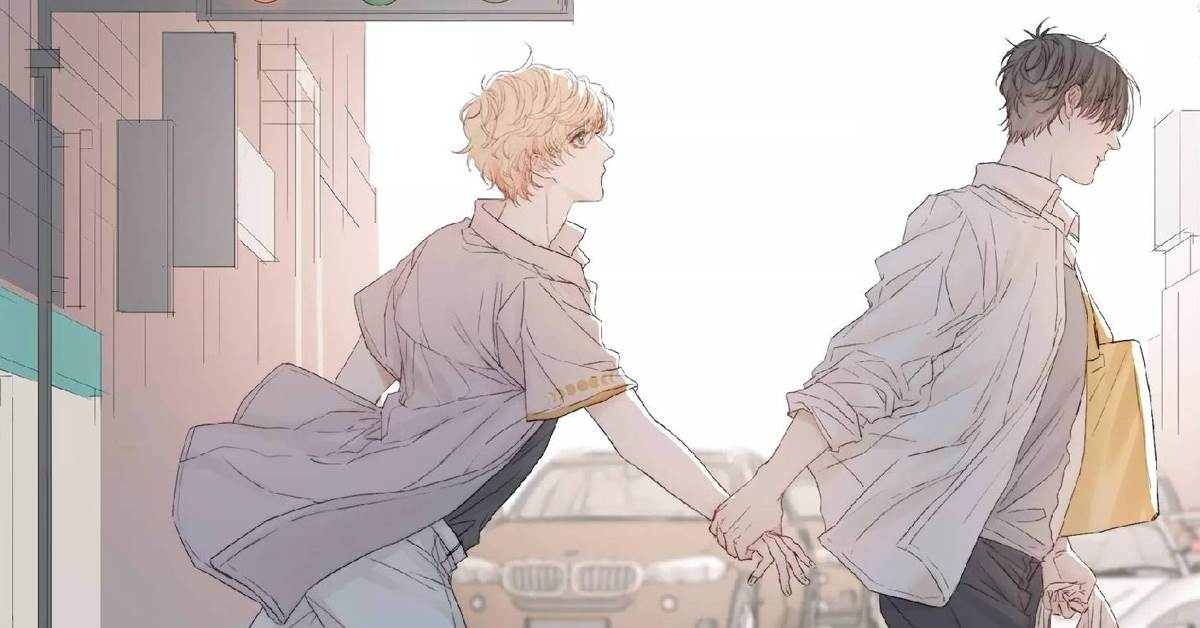《一覺醒來竹馬變男友[重生]》第51章
他給他補課,每天載他上學載他回家,還替他出頭教訓了于小洛,鬧得全校都知道。
朝揚的腦海里有個聲音在不停地叫囂:這麼完美的人上哪去找?趕緊追啊!
同時又有另外一個聲音在勸阻:這麼優秀的人,你配嗎?
朝揚曾肆意沖動過一次。
上一世他轟轟烈烈跌跌撞撞,一腔熱血在蘇秦身上撲得滿身傷痕。
這一次面對廖星辰,他猶豫了。
倒不是他害怕失敗,他是怕失敗后和廖星辰連朋友都沒得做。
他不想他們再回到之前那種相見不相識的關系。
結果是好還是壞,他都不敢拿廖星辰去賭,他舍不得他。
再放放吧,朝揚心想,或許再放一段時間,這份發了瘋的喜歡就消下去了。
……
廖星辰和朝揚抵達市中心某KTV的時候,包廂里早坐滿了人,三十幾顆腦袋分成四堆。
五音不全的體委方振在飆《死了都要愛》,旁邊幾個人捂著耳朵想搶他手上的話筒;另外一堆在猜碼,面前已經七倒八歪空了幾個酒瓶;還有一堆坐在角落組隊打游戲。
沙發的中心位置,徐磊和關系最鐵的幾個哥們在玩骰盅,喊“六個六摘!”的嗓門幾乎蓋過體委的高音。
廖星辰手扶著包廂門,有那麼個瞬間想要退出去。
徐磊看清門口站的人,黑色骰盅往桌上一砸,對宋連飛道:“老宋你死了,你們都死定了,我們東苑的骰盅王來了!”
濱江大院以中間的一個大魚塘為界限,分了東苑和西苑,東苑靠近大門,而西苑在后門,出去就是一個小山坡,那里種了幾棵桃樹。
徐磊廖星辰朝揚就是東苑的,宋連飛和方振是西苑的。
門口只有他和廖星辰,但朝揚十分確定,徐磊口中的“骰盅王”指的絕對不是他,他根本不會那玩意兒。
以前蘇秦生日的時候很愛和林子老高玩骰盅,朝揚也想加入他們,結果玩了兩圈就被蘇秦嫌棄的趕到了一邊。
廖星辰在心里給徐磊又記了一賬,再多集兩筆就能得個【正】字了,可以揍了。
他推著朝揚走進包廂,長腿跨過西苑那幫人,踢了踢徐磊示意他讓位置。
徐磊故意往旁邊人身上倒了一下,沒動,說:“沙發太小了,你們倆擠點坐。”
說完把骰盅遞上去。
朝揚幾乎是貼著廖星辰坐下來的,廖星辰把手往后一放,遠看就像是他摟著他,姿勢親密無間。
廖星辰從徐磊手中接過骰盅,贊許的看了他一眼,心里的那個【正】字又少了一筆。
來的都是準醫學生,沒一個人是抽煙的,包廂里的空氣干凈不渾濁。朝揚和廖星辰兩人都是在家洗了澡才出的門,這會兒離得那麼近,彼此身上的味道清晰可聞。
一個是甜淡的柚子味,而另一個是清冷的薄荷味。
朝揚被那薄荷香攏得心猿意馬,想換位置又舍不得,只得抿著唇,每隔幾分鐘轉頭呼吸一下新鮮的空氣。
初秋的夜晚微涼,廖星辰穿了件七分袖的灰色T恤,他長腿曲折,一只手搭在膝蓋上,另一只手扣著骰盅。
身上的氣場瞬間就讓周圍都靜了下去。
“玩什麼?”
西苑代表宋連飛以前和廖星辰玩過一次骰盅,知道這人狡詐得很,便悄無聲息地把賭注調小:“大家都是鄰居,一次半杯吧。
”
倒旁邊的徐磊起來就給他一巴掌:“草泥馬,剛才你跟我玩的時候明明是一次一杯!”
“難道老子和你就不是鄰居了?見到高手來了就慫,我真為你們西苑感到丟臉!”
媽的,玩個骰盅還特麼玩出大院分裂來了,少年人就是經不起激,宋連飛拍臺:“一杯就一杯,誰怕誰!來!”
骰盅其實玩的就是心理戰術,對手喊出來的數字是真是假,全憑猜測,朝揚不太懂游戲的規則,但只是在旁邊觀戰都覺得很刺激。
宋連飛連著輸給了廖星辰幾次,已經要喝吐了。但他身上扛著西苑的臉面,男人不能輕易言敗!
又玩了一輪,廖星辰滴酒未沾,他覺得有點無聊還有點困,余光望見旁邊那位一臉興致勃勃,十分想參與的樣子。
他不動聲色把骰盅挪過去,問:“想玩?”
朝揚連忙擺手:“不不不,我不會玩。”
方振一曲高歌唱完,接著又唱了首《天路》,包廂吵得要死,說話得對著耳朵才聽得見。
廖星辰借機把頭低得很近,嘴唇幾乎要貼到朝揚的耳廓:“沒事,我教你。”
朝揚一動不敢動,憋著氣說:“會輸的。”
廖星辰揣著壞心思逗他:“不怕,輸了我來喝。”
得知廖星辰要讓朝揚上場,他來頂酒,宋連飛又清醒了,感覺報仇的機會來了。
畢竟朝揚是整個大院成績最差,但是最乖的孩子,別說骰子了,這人連斗地主都踏馬不會。
宋連飛:“揚揚別怕,來,我會給你放水的!”
既然都這麼說了,朝揚當然得上,他早就想玩兒了:“老宋,你可千萬要讓我啊!”
說完把骰盅搖得哐哐響,氣勢挺足,廖星辰都被他這個新手模樣給逗笑了。
一頓操作猛如虎,打開一看只有三四五,朝揚看著自己搖出來的散裝數字,欲哭無淚,他求救地望向廖星辰:“這怎麼喊啊?”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